發布時間:2020-02-11所屬分類:醫學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1932年,霍亂疫病在天災人禍中橫行全國。本次嚴重的疫情吸引了當時傳媒的高度關注,得到全國性大型報刊及一些地方主要報刊持續報道,留下重要史料。盡管國民政府也及時在區域核心城市采取了一系列抗疫減災措施,包括海關檢疫、衛生控制、推廣注射疫苗
摘要:1932年,霍亂疫病在天災人禍中橫行全國。本次嚴重的疫情吸引了當時傳媒的高度關注,得到全國性大型報刊及一些地方主要報刊持續報道,留下重要史料。盡管“國民政府”也及時在區域核心城市采取了一系列抗疫減災措施,包括海關檢疫、衛生控制、推廣注射疫苗,但是廣大的邊緣鄉村地區因為衛生防疫資源的匱乏而難以克服疫情,從而造成了普遍性的大恐慌,陷入普遍失序。由于缺乏醫療資源,在面對疾病時大多數邊緣地區被迫采取了非理性應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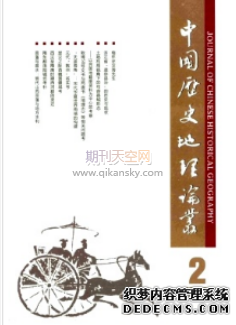
關鍵詞:霍亂;衛生防疫;社會恐慌
近年來,隨著社會史研究的復興,尤其是“非典”的沖擊帶來對人群生命史的反思,中文學術界對于醫療社會史的興趣也漸萌發。但是諸多著作都是通史性的,涉及霍亂問題的著述僅僅占據一席之地。近代以來的醫療史研究較為薄弱,而1932年席卷全國的大型霍亂疫情,更是研究甚少。就目前民國醫療史中所涉獵到本次災難的研究來看,從研究地域上看已經形成了區域劃分,如石雪婷重點關注1932年霍亂的重災區陜西省,強調政府在疾病防疫工作中缺位導致疫情的擴散蔓延,并提出本次疫情對于陜西省公共衛生體系建立的促進作用[1]。還有從研究內容上看,包括了疾病觀念,如孔偉就從寧波地方性新聞報道中入手,考察1932年的瘟疫對人民的疾病觀和衛生觀念形成的推動作用[2]。同樣的還有李偉提到全國性報紙《申報》對于公共衛生事件的關注,部分章節強調了1932年瘟疫促進了民眾公共衛生觀念的成熟[3]。除此之外也不乏對于衛生防疫的政策措施的關注,主要是政府的瘟疫應對和社會團體的社會救濟[4]。
通過對以上論著的簡單梳理,可以明顯發現,對于作為瘟疫承受主體的普通民眾尤其是鄉村地區的農民,在此前極少被人關注,即使是一些研究疫情災難下社會防疫應對的論著,也只不過是將民間社會作為社會群體的一部分匆匆略過其應對。對于1932年洶涌疫情之下社會大觀缺乏清晰的認識,過于強調政府的應對卻少有關注鄉村。鄉村的居民們在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一直處于虎疫威脅的恐慌之下,由此作出了許多非理性之舉,但這一方面鮮有人進行挖掘。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可搜集的一手資料對當時疫情下官方的抗災防疫措施和鄉土社會的恐慌的形成、表現、分布差異狀況進行探究,向瘟疫時期的社會真相更進一步,可以了解城市與鄉村兩個不同緯度的防疫自救嘗試與其作用。
一來襲:1932年霍亂的爆發與蔓延
1932年,突如其來的霍亂瘟疫爆發,并且在社會大眾普遍缺乏公共衛生觀念和衛生防疫條件惡劣的社會背景下迅速擴展蔓延,給全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傷痛。
霍亂(Cholera),又被時人直接音譯為虎烈拉,或是形象地稱呼為虎疫,是一種源自恒河流域與布拉馬普特拉河三角洲一帶的急性傳染病,并且在1817年有過大規模的爆發[5]。大致在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霍亂病菌經由海路交通傳入中國。這不同于傳統中國醫學語境下,將夏秋時節的急性腸胃炎和食物中毒定義為“霍亂”,而是真正由霍亂弧菌所傳播的一種烈性傳染病,并被當時清人的筆記小說和地方志普遍記錄下來[6]。
(一)1932年霍亂的傳播
就現今的資料來看,1932年的霍亂疫情首先發現于口岸城市武漢和上海。在此前一年,1931年8—9月間,長江潦災遍及七省,漢口成為一片澤國,大量水災難民從武漢涌入上海,衛生堪憂,密集的人口流動誘發了疫情。當時便有人意識到了其中的瘟疫隱患[7],但是從后來嚴重的霍亂疫情可知,這樣的真知灼見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也沒有能夠成功阻止霍亂的爆發。事后回顧,是當年4月23日武漢先出現疫情,后于4月26日上海出現疫情,而且當年霍亂疫情來得格外早,以至于正常的預防注射工作未及開展,使得霍亂快速擴散蔓延[8]。而對當時的公眾來說,首次從報刊上看到霍亂的消息是在5月5日《申報》的報道《上海發現真性霍亂》中,這篇報道只簡要提及今年霍亂疫情出現之早[9],可見當時全社會都沒有足夠重視這次霍亂疫情,也根本想象不到不久之后竟會大難臨頭。
大致可知,1932年的霍亂疫情是由前一年長江流域大水災引起的,在入夏疫病高發期首先爆發在工商業繁榮、對外交流頻繁、交通便利經濟發達的大城市里。很快,病菌乘著長江交通蔓延開來,從水災地漢口迅速傳播到上海,被關注之時病禍已成燎原之勢,一發不可收拾。如今根據所收集的資料,還能夠清晰重現在傳染病情爆發的早期,即5月至6月間疫情是如何在各大城市中傳播肆虐的(見表1)。
分析可得霍亂傳播的大致圖景,首先是前一年的長江水災使得湖北武漢成為霍亂之濫觴,接著疫情暴發之后,病菌沿長江水路傳入上海,最后憑借上海交通樞紐的通達性,沿著鐵路傳染北方及內陸地區、沿著海路傳染東南沿海,同時向南向北輻射傳染。整體傳播趨勢是先在交通便利的核心城市之間傳播,然后才逐漸擴散至小城市乃至鄉間。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傳染病的肆虐很少傳播到中國西北,但伴隨著隴海線靈潼段的建成通車,病毒也有機會沿著鐵路線感染了關中土地[10],并且進一步在西北擴散,甚至到九月份其余地方疫情稍殺之時,青海西寧又以疫情告危[11],這給整個西北地區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另外一點是,盡管在新聞報道中被關注的病例都集中在各大小城市,但是這并不代表廣大的鄉村地區就沒有出現霍亂疫情,享有優先醫療衛生服務的軍閥閻錫山也沒能幸免,何況是普通人。考慮到民國時代教育普及度不高,報刊的目標讀者主要還是城市讀者,因而鄉村地區疫病情況報道少更有可能是在重要性的權衡取舍中得不到當時報紙編輯的重視。下文中對于廣大鄉村地區霍亂恐慌的闡釋可以側面反映出鄉村地區的受災情況之嚴重,因而1932年的“虎烈”疫情毫無疑問是一場波及廣泛的全方位大瘟疫。
(二)霍亂疫情造成的損失
這次前所未見的大瘟疫也造成大量死亡病例。根據時任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伍連德在霍亂期間的統計,1932年的霍亂瘟疫侵襲了23省,312個大城市,有十萬個被記錄的病例及約三萬四千人死亡[12]。對此,有衛生署當年所報告的受災城市統計表可加以印證(見表2)。
然而這數字是肯定被嚴重低估的,按余新忠的觀點,受當時統計條件限制,大部分缺乏醫療服務機構的地區無法給出病例及遇難人數的數據,或者還有許多病情輕微的病例不被統計在內。基于此,余新忠根據大量報刊的新聞,進行累加估算,因災罹難的人數已達到數十萬人[14]。所以,“民國”廿一年的虎烈之災,無論是在波及的地域范圍還是造成的人員死亡數量上,都稱得上是民國時代最嚴重的瘟疫。
二撲殺:核心城市的有限防疫措施
站在城市的視角上審視1932年霍亂疫情期間的應對表現,可以看到“國民政府”積極行動在大城市里推行了一系列抗災防疫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因為資源有限分配不均,對于疫情的整體控制效果并不理想。“國民政府”內部派系軍閥眾多,本就難以政令暢通,加之區域間發展不均衡,在面臨疾病威脅時所能夠動用的救災力量也不一樣,故本文在此只選取部分發展程度較高的區域核心城市加以論證。
1932年瘟疫期間,南京“國民政府”并非毫無作為束手待斃,相反,南京國民政府從成立之初,就一直重視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早在1928年,就頒布過《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組織法》,這是設置衛生行政專管機關的開端,填補了北洋政府時期沒有單獨衛生防疫行政部門的空缺,并且還明確了“衛生部”的職責包括了傳染病的調查、預防和撲滅,海港、航空、車船的檢查防疫[15]。
在嚴重的霍亂病情爆發之后,政府迅速反應,積極投入到防疫和救治工作中,綜合了當時由英法兩國提出來的西方先進霍亂防疫經驗,包括法式做法以嚴格檢疫防止霍亂,以及英式做法以大力改善環境衛生來阻斷霍亂傳播[16]。在此認知基礎上,“國民政府”除了救治病人之外,主要推行了海港檢疫、公共衛生控制、防疫注射等抗災防疫措施。
(一)海港檢疫
在中國,海關檢疫一直籠罩著一層濃濃的政治意味。歷史上由于海關主權的淪喪,中國的海港檢疫工作一直由外國人把持,但是以伍連德為首的有識之士們一直強調收回海關檢疫權的重要性并且一直在為之努力著。1931年1月1日起“國民政府”開始先后收回廈門、汕頭、牛莊、長江漢口與安東的檢疫權,1934年起又陸續收回天津、青島、大沽、秦皇島等沿海沿江各口岸的檢疫權,建立了相應的衛生檢疫所。從此,國境海關衛生檢疫權交回中國政府管理,結束了各自為政、條規不一、業務混亂的狀況[17]。
1932年的霍亂爆發蔓延之后,海港檢疫工作部門迅速反應過來,在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統一調度指揮下,各地區的港務檢疫工作很快就運轉了起來。由于上海是最早的爆發地和最重要的港口海運樞紐,因此海港檢疫處下令廈門、汕頭、青島、天津、廣州等處碼頭,對經滬港而來的船只嚴加檢疫[18]。同時,設立在上海的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在入夏進入疫期以來,也積極對各地入滬船只以及外國船只嚴加檢疫,嚴防外來病源輸入,在全體的努力工作下,瘟疫期間每日可檢疫二十五艘船,一定程度上斷絕自海港輸入病毒的源頭(本處所提日檢25艘船為疫期工作量。在1932年的上海海港檢疫處工作報告中提到,1932年共檢疫中國船只108艘,共196098噸,英國船只755艘,共5138396噸,美國船只210艘,共2287675噸,日本船只712艘,共3666880噸,挪威船只148艘,共642497噸,芬蘭船只57艘,共410291噸,德國船只82艘,共631847噸,法國船只58艘,共723381噸,其余船只114艘,共770875噸。可見上海的海港檢疫工作重心依然是放在對外上。參見伍連德報告:過去一年海港檢疫成績[N].申報,1932-12-16(11))。但是從數量上看,海港檢疫工作的重點仍然是外來船只,更有可能攜帶傳染病菌的中國船只并不是檢疫的重點對象,且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海港檢疫工作的順利進行,因而不宜過分夸大其防疫減災的功效。
(二)公共衛生控制
霍亂得以肆虐的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惡劣的公共衛生環境,得不到保障的飲用水和食品衛生是滋生霍亂的誘因,因此在公共衛生控制方面,政府也花費了大力氣進行整治。
惡劣的衛生條件源于民眾的貧困與衛生觀念淡薄,因此不注重飲食的衛生,進而攝入受污染的飲用水或者食物導致霍亂的傳染。同時,對于居所環境的漠視,也導致了病毒的擴散和傳染。因此,各地的政府部門都積極采取了應對政策。
在上海,伍連德率先要求自來水降價,令平民能享用干凈的水源,避免食用水受污染而感染[19]。在天津,公安局嚴令清道夫清潔街道,取締街頭小販的不潔食物,還要公眾注意用生石灰對患者居所進行消毒并且及時送患者就醫[20]。在廣州,衛生局下令禁售魚生、雪糕、剜雪涼水、涼粉等生冷食物,以及禁止擺賣切開及腐爛的水果。社會局向公眾宣傳消毒的重要,提出對患病者的居所用消毒物料進行徹底消毒[21]。在西安,防疫院統籌的清潔運動也開展了,由公安局主辦用石灰大消毒,禁絕瓜果售賣并且嚴行檢查蔬菜,擴大宣傳并且禁止在城內埋葬死者[22]。
期刊推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季刊)創刊于1987年,是由教育部主管、陜西師范大學主辦的目前我國歷史地理學科定期刊物,全國中文核心期刊。本刊主要登載有關歷史地理學基本理論和方法研究、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地名學研究、方志學研究、古都學研究、歷史地理學史研究等方面的學術論文以及歷史地理學和相關學科重要的學術動態、學術評論、資料索引和出版信息等。
但是被記錄下來的公共衛生控制措施都是施行于大城市中,這實際上還是片面的,真正迫切需要改善惡劣衛生環境的是鄉村地區。然而由于市政資源的分配失衡,鄉村地區的衛生措施幾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沒能切斷霍亂的傳播渠道。
(三)防疫注射
防疫注射也是控制病情蔓延的一種重要手段,各大城市本就存在夏季的日常自愿防疫注射,在疫情蔓延之后,各大城市紛紛出現了延長注射期、強制注射的情況。
比如在廣州,從廣州市政公報中可以看出,日常的自愿霍亂防疫注射本來僅安排在六月一日至十五日,但是自霍亂大規模爆發之后,疫情很快被官方察覺,政府敏銳察覺到了周平均死亡人數比起去年激增的事實,從而認識到了霍亂的嚴重性,因而政府很快就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就包括了延長免費注射期,注射從六月十五日截止,多番展期直至七月三十一日[23]。在其他城市,比如天津,從七月一日起由慈善組織天津市救濟事業聯合會協助紅十字會出資推行免費注射,至七月七日,則有公安局下令強制推行全面防疫注射[24]。在西安,為了擴大注射的普及范圍,政府則是不斷增加注射地點,在七月二日于民眾教育館開始推行免費注射之后,又將省立醫院也納入注射范圍,還成立了臨時防疫醫院統籌防疫事務[25]。
唯有上海情況較為特殊,因居民素質較高以及醫療常識的普及,市民并不陌生預防注射,因而不必推行強制政策,在疫情暴發前后也有一百萬以上的人接種了霍亂疫苗[26]。
一系列抗災防疫措施的推行得到了一定的成就,在各大城市里,霍亂疫情最終都被撲殺,而且死亡人口也得到了控制。以至于在最早暴發疫情的上海,其實受災情況并不嚴重,在七月二十八日統計的死亡率僅為6.4%[27]。伍連德博士在霍亂疫情之后制作的報告里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見表3)。
但是,這樣的成績是醫療資源的傾斜導致的,在有完善市政服務和現代公共衛生制度的上海,有財力也有能力應付霍亂虎烈,能在疫期免費安裝26個給水栓,并出動5輛運水車為居民們提供干凈飲用水,還能夠由衛生管理機構大規模推行疫苗接種,并且還印刷散發了上百萬份傳單和海報加以宣傳,前后發布十八期防止霍亂公報時刻監控疫情,因而在上海疫情尚且能夠控制[29]。但是在其他地方,疫情則是要嚴重得多,就病情嚴重程度、死亡人數而言,南京是上海的十倍,杭州是上海的二十倍(此處數據為1932年9月統計所得,與表3的統計時間不一致,因而數據可能存在偏差。參見各省市霍亂流行情形及防治狀況[N].大公報,1932-09-14(8))。京杭尚且如此,廣大的鄉土社會,情況只會更加慘烈。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