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關鍵詞:開端;直接性;間接性;普遍性;特殊性;確定性;不確定性 摘要: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提出了關于科學之開端的問題,這個問題與直接性和間接性密切相關。直接性和間接性具有內在性和自我確證性的統一,能使我們到達純粹的存在,這種純粹的存在一定是在知識
關鍵詞:開端;直接性;間接性;普遍性;特殊性;確定性;不確定性
摘要: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提出了關于科學之開端的問題,這個問題與直接性和間接性密切相關。直接性和間接性具有內在性和自我確證性的統一,能使我們到達純粹的存在,這種純粹的存在一定是在知識中首先出現的規定性,并成為純粹的開端。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進一步論述了關于間接性和直接性的開端問題,第一個環節是作為直接性、不確定性的普遍性,第二個環節是作為間接性、確定性的特殊性,第二個環節寓于第一個環節之中,它們共同構成了第三個環節,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這實際上是直接性和間接性的對立統一,而開端則寓于它們之間互為前提的邏輯推論的形式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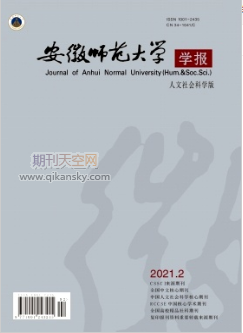
“請問我們從哪開始呢?白兔問。‘從開端開始。’國王嚴肅地回答說。”在劉易斯·卡羅爾的《愛麗斯漫游奇境》中,國王的回答讓我們聯想到了另外一個回答,這個回答是由現代哲學的“君王”黑格爾在“科學必須以什么為開端”這個標題下所給出的。黑格爾的哲學“魔法術”在于從智慧之帽中引出白兔所提出的開端問題。眾所周知,在黑格爾的哲學中,開端問題是爭論的焦點,一百個不同的黑格爾研究者將會給你一百種不同的回答,這些回答有時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然而都是一種巴比倫式的喃喃自語。下面我將嘗試給出一種詮釋,更確切地說,從以下若干問題入手,組建對開端問題的詮釋。
一、科學必須以什么為開端?
在《邏輯學》的導言和“科學必須以什么為開端”一節中,黑格爾延續了其耶拿時期所進行的反思,并賦予它們一種圓圈式的論證方式。直到今天,人們才真正搞清楚,黑格爾提出似是而非的第三種哲學的意圖是什么,這種哲學既非獨斷論,也非懷疑論,既非實在論,也非建構論,而是兼而有之。他提供了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在開端就被固定下來了。
如果哲學的起點是確定性的、間接性的東西,它就不能把自身設定為開端,因為它會預設某種東西以便證明這種開端的正當性,這樣,它將陷入相對性的無限后退。如果哲學的起點是不確定的、沒有根據的、直接性的東西,那么,它就相當于純粹斷言的獨斷論。基于耶拿時期已經展開了的論證,黑格爾一開始就堅決反對那種“來自內在天啟、信仰和理智直觀”的任意假定的開端[1]65-66,反對雅可比和謝林,雅可比和謝林從一開始就忽略了邏輯方法,并因此放棄了達到確定知識的希望。相比之下,費希特比較徹底一貫的先驗唯心論被譽為“使理性從自身表現其規定性”。[1]41在《邏輯學》的導言中,超越意識對立的原理被強調了三次,并且黑格爾以純粹知識、純粹概念為開端并不被視為臨時性的假設或者僅僅是斷言,而在《精神現象學》的理論步驟中獲得了合法性及其證據。1831年出版的《邏輯學》第二版證實耶拿時期的《精神現象學》提供了純粹科學的概念演繹,提供了哲學開端的概念演繹,并因此也提供了邏輯學開端的概念演繹。然而,有了《邏輯學》,在《精神現象學》中得以完成的作為攀登“階梯”的懷疑論就可以被擱置一邊。
表面看來,邏輯開端可以通過兩條路徑提出,一種是間接的,一種是直接的。早在“科學必須以什么為開端”這部分,黑格爾就強調指出了這兩條路徑。基于《哲學全書》,他著重指出,“無論是在天空中,還是在自然界,或者在心靈內,以及其它任何地方,都沒有什么東西不同時包含間接性和直接性,因此,這兩種規定性表明它們自身不曾分離過、也不可分離,而它們之間的對立便什么也不是。”[1]68
在某種程度上,黑格爾和奧德修斯一樣希望擺脫困境。奧德修斯這位古代的英雄設法擺脫了潛伏在墨西那海峽兩岸的“斯庫拉”和“卡律布狄斯”這兩個怪物。①在黑格爾的《邏輯學》中,開端問題在很多方面讓人想起奧德修斯的無畏事業,知識既要避免成為“斯庫拉”(直接性)肆意吞噬的祭品,又要避免成為“卡律布狄斯”(間接性)貪婪觸角的亡靈。話說回來,當代哲學中也存在著這樣的困境,即實在論與建構論,這一困境就像古代的墨西那海峽一樣,兩岸之間的路既狹窄又危險,而實在論與建構論就像兩種同樣邪惡的亡靈,都是需要避免的。
二、間接性與直接性
在黑格爾的《哲學全書》第12節,我們看到,間接性和直接性這兩個環節“表面上雖有區別,但兩者既不可缺一,又不可分離”。[2]56《哲學全書》第65節反駁直接知識和間接知識的非此即彼,按照黑格爾的說法,這種非此即彼依賴于直接性與間接性之間的對立邏輯。“整個邏輯學的第二部分,即本質論,討論的是直接性與間接性內在的、自我確證的統一。”[2]156
在這里,開端的問題也不能夠違背黑格爾所勾勒出的方法的基本原則,不能違背概念的內在結構——自我指涉的否定性(self-relatingnegativity)。所以,非此即彼的可能性被排除了,我們既不能從純粹的直接性開始,也不能從純粹的間接性開始。即使這兩個環節看起來有所區別,它們也必須被理解為不可分割地相互關聯在一起。因此,黑格爾提供了關于一種開端的兩種“變式”、兩種“視角”、兩種邏輯路徑,而這兩種邏輯路徑在其各自的片面性中是兩個環節,同時又包含著其對自身的揚棄,包含著自身中的否定性,并因此建立了直接性和間接性的同一與統一。
在間接性版本中,《精神現象學》這本書的結論扮演了邏輯開端的角色,這個開端以包含于《精神現象學》對純粹知識和概念式把握的思維之立場的證明為中介。所有其它可能的起點——意見、情感、信念、觀念等等——都被排除在外了。在這一方面,《精神現象學》是《邏輯學》的前提,它借助于對意識范式的否定,借助于“懷疑論”的面向,使開端合法化,把相對性和間接性揚棄于純粹的、概念式把握的思維之中。這樣,“結果”就直接回到了“開端”,結束回到了開始。這種間接性路徑的結果是對間接性的揚棄,所得到的是純粹的概念把握的知識,這種知識作為簡單的直接性,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規定。間接性包含著把自身揚棄于純粹的直接性之中。
在直接性版本中,開端被直接提出來了,亦即決心要純粹地去思維、去思考思維本身。這種“決定”(Ent-Schließen,字面意思是“解除封閉”)意味著“開啟”,意味著直接設定,意味著發端的思維之“在”(is),除此以外別無其它。實際上,在做出決定之前,根本就不可能討論“實存”(existence),黑格爾主張“構成開端的東西”和“開端自身”是同義的。[1]75于是,作為最初直接性的純粹的存在就被設定和主張了。在這里,沒有什么前提,沒有間接性被主張。無論如何,純粹存在的在(is)和實存是一種規定性。絕對的直接性被證明如同絕對的間接性一樣。通過演繹的必然進程,開端失去了它在最初的規定性中所表示的東西,也就是說,成為某種不確定的、本身抽象的東西。即使純粹的知識也是消極的規定性,其自身具有否定性,因而具有不確定的存在這種最小的規定性——否定即肯定。
俗話說,條條道路通羅馬,上述兩種情況都能夠讓我們到達純粹的存在,而這種純粹的存在一定是在知識中首先出現的、直接的、簡單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仍然是未定的,它才是純粹的開端。鑒于此,黑格爾宣布了最終的論證,剩下的工作就僅僅是解釋和說明了。開端的合法化聯合了片面的間接性和同樣片面的直接性,聯合了“前提”和“無前提”,這兩種變式都通往純粹的在(is)和純粹的存在(Being)。嚴格說來,《邏輯學》開始于純粹的概念把握式思維,以及從而被設定的思維之純粹的在(is)。《邏輯學》包含的也僅僅是純粹的自我把握這種思維,僅此而已,以存在為形式,它始于此種思維。舉個例子來說,無論誰決定去下棋,無論誰將自己敞開給游戲,都通過它們的開啟行動顯示了他們去下棋的決定,然而,這一點涉及到了作為一個前提的(下棋)思維,它必須遵守游戲的原則,即游戲規則。
純粹的存在表明了概念的最小定義。這“最初的”存在,即直接性,它在自身之中,將自身定義為不確定的,僅僅定義為與自身相等同,而沒有進一步的規定性。當一個人說“沒有進一步的規定性”時,意味著至少給出了一個規定性,而排除了進一步的規定性。
黑格爾在其最高級的運用中堅持了這一最低限度:存在是“最為貧乏的和最為抽象的”規定性;因為就內容而言,在這里,思想“無外乎”是純粹的存在。[2]136在概念中,我們最起碼能夠指出所有最貧乏、最抽象的原初規定性,在這里,我們恰恰在表面上看到了作為確定性的不確定性和作為不確定性的確定性之間的矛盾。這樣的開端作為開端,在其徹底的簡單性之中,在其單純的存在規定性之中,只能是最空洞的規定性。同樣,《精神現象學》曾經也是從最直接、最貧乏、最抽象的形態開始的,即關于“是”什么、“意謂著”什么的簡單意識,這種貧乏是其唯一的財富,并且注定會消失。邏輯學的開端可以被描述為普遍性、特殊性和個別性之間的原初統一,在這種原初統一中,這些環節尚未通過其展現而區分開來;盡管它們尚未獲得充分規定,但已經在起作用了,相等作為最抽象的普遍性,抽象差異作為不確定的特殊性,單一性作為規定不充分的個別性。這種極端缺陷需要相應的語言表達,但這里不可能有命題或判斷,只有“存在”這個簡單的語詞,一個驚嘆,以及把一個句子轉換成一個驚嘆,在這里,它指的是一個孤立的語詞,一個概念的最小語言原型。那么,開端出現了,它自身是有不足的,可以說極其不足:簡單的開端被“設定為被否定所困擾”[3]555——(這里指的是一種)最不足的、最貧乏的否定定義——純粹的否定——虛無(非實存)。
這是第一步,這樣一種出發點仍然保持直接性,因為“存在”在這里被直接設定出來,而“無也只有在有中直接出現”[1]104。這種最高級不能擺脫確定性、間接性以及內在于其中的關系。邏輯上的第二步,也就是“第二個問題”,即否定性①,被證明是一個原初的“第一困擾”:純粹的存在被設定為被否定所困擾,“無”同樣與其自身純粹等同。在語言學詞匯中,就像說“存在—無”(Being-nothing)一樣,兩個相反的、互相排斥的語詞合并成一個矛盾修辭格,某種機智而愚蠢的東西、或某種“不可說的可說”(歌德語)。
相關期刊推薦:《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創刊于1957年,是安徽省教育廳主管,安徽師范大學主辦的教育綜合類學術期刊。設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詮釋學、中國詩學、徽學、教育創新、道德建設、哲學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等欄目。
在黑格爾看來,“有”與“無”是同一的,是絕對等同的,是最小的統一性(同一性),然而在第一個問題“有”與第二個問題“無”之間存在著“完全抽象的差異”,這樣,這種區別(非同一性的原初形式:差異)和矛盾(對立)的最小形式就被表達出來了,這就是邏輯上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僅此而已。每一個事物自身帶有否定性,并且直接“消失”到其對立面之中,這是第一個抽象的最小運動,作為一個原初邏輯的運動,黑格爾稱之為抽象的變易(Becoming)。因此,開端必然包含存在與無在變易中的統一及其否定性和實存,其中存在與無首先將其自身展示為環節。黑格爾將其描繪為“第一個真理”,它構成了下一步的基礎:作為反身的否定性,“存在”和“無”是其自身的他者之原型,是它們在根本上缺乏規定的邏輯形式。與自身相關聯的否定性被證明是邏輯的基本構成,是“自由”概念本身的生殖細胞。
這一點在《邏輯學》的“注釋”部分被闡明了,在那里,黑格爾討論了哲學史的關鍵環節,但是,黑格爾是在邏輯順序上進行討論的,而不是在時空歷史順序上進行討論的——首先,討論的是巴門尼德的存在,第二,討論了佛教的無,第三,討論了赫拉克利特的深刻思想,赫拉克利特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即在變易中,揚棄了存在與無簡單而又片面的抽象性,但是他是在最小的抽象形式上這樣做的:一切皆流(pantarhei)。②另外,黑格爾還列舉出了一些例子,它們是對于存在和無在語言上公然而空虛的誤解,即把它當作某種東西,有與無必須在根本的、在被提及的極端抽象中嚴格地當作抽象的“思想之物”,而不是被當作具體之物。若假定對它們而言存在著更具有規定性的東西,這是荒唐的、無意義的,這與“這所房子是否存在?這100個泰勒是否屬于我?”這樣的問題看起來是等同的。
隨著對立面的“初步”的、最低限度的統一,概念的基石就被確立下來了,這是進一步的思想之規定性內在運動的基礎,是知識“自我建構之路”的基礎。科赫(AntonKoch)聲稱,作為《邏輯學》的展開,對其開端的理論理解是逐步擴展的。一開始,我們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知道得非常膚淺,我們僅僅了解對于開端而言必要的東西,然后才往下有序地進行。這樣,我們就有可能將“前提”和“無前提”統一起來,以便去避免不合理的預設和獨斷論式的干擾。然而,接下來的步驟必須要顯示出邏輯上的嚴格性,特別是在它們的過渡中,這是對新的概念邏輯而言另外一個不可避免的挑戰。
三、實踐哲學的開端
在黑格爾的哲學中,最具說服力的段落是《法哲學原理》導論的第5節至第7節,這部分巧妙地證明了黑格爾關于自由意志及其行動的哲學理論之邏輯基礎,亦即黑格爾實踐哲學的邏輯基礎。另外,在這里還可以看到直接性與間接性之間關系的清晰展現,這對于黑格爾整個的哲學思維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作為法權科學的原理和開端,自由意志概念的基本定義只有重新回到黑格爾的邏輯學才能得到有意義的、全面的理解。
意志概念的規定性,即基本的三一式(triad):
α)普遍性:相等,無差別,同一性
β)特殊性:不等,差異,非同一性
γ)個別性: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同一
在主觀精神的終點,產生出了(客觀精神)的起點,即普遍概念,它是作為真正自由意志之首要形式的自我,是自我設定的直接個別性,它被提升到了普遍性。自我的直接性源自于對任何特定內容總體上的拒斥,在《法哲學原理》的第5節中,它被明確表述為作為自我反思自身的自由意志,表述為對自身純粹思維的自我。《法哲學原理》和《邏輯學》幾乎用同樣的方式將意志的第一個環節展示為一個思維著的自我:自我“首先是一種純粹自我相關的統一,它不是那么直接,而僅僅是從所有確定性和內容中抽象出來的,后退到與自身完全等同的自由。就此而論,它是普遍性”。[3]253無規定性、抽象的同一性是唯一的規定性,而這種無規定性被發現于同一性的規定性之中。在這種純粹思維中,我希望我自己達到普遍性,我希望我自己排除所有特殊性,我希望在自身之中保有作為可能性的規定性。但是,第一個環節“自身并非沒有規定性,它是抽象的片面之物,這構成了其規定性”。[4]52①
意志的概念仍然未被充分規定,盡管如此,我們應該記得《邏輯學》中引用過的一句話:“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規定性。”它卻絕不可能是徹底的無規定性或純粹的直接性,相反,它恰恰是某種最低程度的規定性。在此我們應當稍微停頓一下,因為在這里,我們所遵循的完全是黑格爾邏輯學的基本論證及其實踐哲學的指導思想,即黑格爾哲學的支點:直接性與間接性,普遍性與特殊性,這些都將它們的他者包含于自身之中。這樣,我們就具有了矛盾的萌芽,而這是必須要揚棄的。只有這樣,從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可以說完全是無規定性——到特殊性的邏輯過渡才有可能。首先,這是一個“從任何規定性中抽離出來的絕對可能性”的問題,在這種“規定性中,我可以發現我自己,或者我可以建構我自己”。[4]51自我作為潛在的行動主體、創始人、無條件的和無規定性的發起者而出現。然而,第一環節缺乏有效性的維度,它仍停留在假定的純“理論”領域,因此,自由仍然只是絕對的可能性。對于意志而言,在思維的第一步中,它的對立面反常地出現了——一個靜止的、不必要的閑置之物。自由的這種否定性的、“理論性的”面向只是一個必要但不充分的定義。——論文作者:KlausVieweg1,3/文,朱光亞1,2/譯,牛文君1/校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