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8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如何達到德福一致的倫理目標是倫理領域思考的重要問題。然而,無論是以福為德還是以德為福的倫理主張,均未達到德福一致的倫理目標。這些主張只是將幸福視為德性,或者將德性視為幸福而已。若要達到德福一致,不僅需要倫理行為者擁有德性,而且還需要倫
摘要:如何達到“德福一致”的倫理目標是倫理領域思考的重要問題。然而,無論是“以福為德”還是“以德為福”的倫理主張,均未達到“德福一致”的倫理目標。這些主張只是將幸福視為德性,或者將德性視為幸福而已。若要達到“德福一致”,不僅需要倫理行為者擁有德性,而且還需要倫理規范作為支撐,否則“德福一致”的目標無法實現。如果說,德性與倫理規范是“德福一致”倫理實現路徑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研究者為追尋該問題展現了一種理論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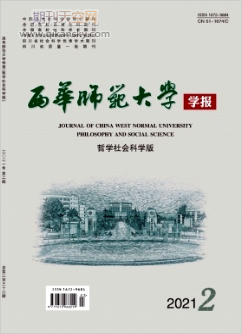
關鍵詞:以福為德;以德為福;德福一致
德性與幸福的關系是倫理研究領域中既古老又年青的問題。一方面,對該問題的思索能夠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說、伊壁鳩魯主義以及斯多葛主義的倫理觀點;另一方面,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研究領域又賦予該問題以新的含義。可見,對德性與幸福的關系問題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以如何達到“德福一致”的倫理目標為研究主題,結合當代西方美德倫理理論對德性與幸福的關系問題展開研究。就“德福一致”的倫理目標而言,伊壁鳩魯主義的“以福為德”和斯多葛主義的“以德為福”都不能實現。因此,本文的研究結論是,“德福一致”的倫理實現路徑表現為,倫理行為者應在有德性的基礎上按照倫理規范的要求行事。
一、德性與幸福的學理考辨
關于德性與幸福的問題歷來是倫理學領域思考的重要主題。無論是基于道德要求,還是訴諸于倫理規范的約束力對倫理問題的思索,都和德性與幸福的問題緊密相關。在倫理生活中,人們普遍關注的是遵循倫理規范行事能否獲得幸福,或者說,一個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是否能夠獲得幸福的問題。通過倫理的維度思考德性與幸福的問題,它不僅是理論層面上的探索,更是對倫理具體行為實踐方面的追尋。然而,若要真正理解德性與幸福的問題必須要了解它們各自的含義,否則很難解釋清楚德性與幸福的問題,進而也無法詮釋為何思考德性與幸福的問題。
依照史家的觀點,在歷史的發展中德性與幸福的含義并非固定不變的,不同時期人們對德性與幸福含義的解釋有不同的特點。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德性與幸福的含義通過三種不同的生活表現出來,即享樂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用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的話說,“人們似乎是為了表明自身的善良而追求榮譽,至少是來自明達之人的夸獎和有識之士的贊譽,也就是為了德性的緣故追求贊譽。在政治生活中,德性比榮譽是更高的目的。看起來,甚至于連德性也不是完善的,因為,即便在睡著的時候,似乎德性也會消失,或者也有在一生中消極無為的德性。除此之外,那些有德性的人也有時運不濟的時候,除非有人進行狡辯,誰也不會說這種倒霉的生活是幸福的。”[1]8這就意味著,德性和人們的實際生活是緊密關聯的,它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和人們的倫理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即便是對于有德性的人來說,如果脫離了實際生活的因素來思考如何獲得幸福,那么這也只是一種理論層面的假想,難以在倫理生活中得到相應的幸福。因為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德性的現實活動就是幸福,而且德性的現實活動必然是在人們的倫理生活中,否則這種活動無法被稱為幸福。
亞里士多德為德性賦予了兩層含義,一是理智德性,二是倫理德性。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解釋,理智德性是人們通過教育獲得的,它是一種可以通過教化和練習而獲得的德性,而倫理德性則與之不同,它不能通過教育獲得,它是自然生成并和人們倫理生活中的習俗融為一體的倫理德性。可見,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德性與幸福具有如此這般的含義,這也是當代美德倫理學主張回歸到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主要原因。按照當代學者約翰·M·瑞斯特(JohnM.Rist)在《真正的倫理學———重審道德之基礎》(RealEthicsReconsideringtheFoundationsofMorality)中的解釋,“亞里士多德相信一個完美的希臘社會中的適當慣例具有連貫性和可理解性。他還假定,那些慣例建立在(或至少被證明是建立在)一種認為有德性的人可以辨別最佳目的和有德性的人能夠就達到這一最佳目的的手段做出最佳判斷的觀點基礎上。”[2]159這就意味著,亞里士多德是在具體的城邦生活中思考倫理問題的,這種思考絕不是脫離實際生活的抽象思考,而是和人們的倫理生活相互結合的。一方面,就希臘社會中的某些慣例而言,它們必然和當時人們的生活習俗緊密相關,或者說這些慣例就是來源于習俗,因此它們才具有連貫性和可理解性;另一方面,就幸福而言,它必然和人們的德性相互關聯著,因為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所謂的幸福指的是完全和德性的現實活動相吻合的,一旦離開德性的現實活動這種幸福的意義便不復存在了。這樣一來,德性與幸福的問題必然成為人們思考的重要倫理問題,它不僅和人們的實際生活方式相關,而且還和人們所處的倫理共同體緊密相連。亞里士多德之所以強調倫理德性其原因也在這里,因為倫理德性與人們所處習俗相互融合,它決定著人們的倫理生活是否和諧。
除此之外,和德性與幸福的問題相比,摩爾認為“倫理學毫無疑問會關注何為善行為的問題;但是它并不一上來就關注到這個問題,除非它是準備告訴我們何為善,以及何為行為。因為,‘善行為’是一個復合概念,并不是所有行為都是善的;因為有些行為當然是惡的,而另外一些可能是中性的。另一方面,除了行為之外,另外一些事情可能是善的;而且如果它們是善的,那么‘善’就是這些事情和這些行為共有的某種屬性。”[3]8這表明,摩爾對善的分析同樣適用于對德性與幸福含義的分析,如果不能清楚地把握它們的含義,那么解釋德性與幸福的問題將無從談起。事實上,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德性還有功能的含義,將這種德性的功能含義運用到具體的生活行為中才能獲得與之相應的幸福。比如,樂手的德性功能之意就是演奏出優美樂曲的能力,醫生的德性功能之意就是指他所具有的高超醫術,工匠的德性功能之意則代表制作工藝品的技藝,他們將這種能力在現實的生活中實現出來就是一種幸福的體現。
當然,人們之所以思考德性與幸福的問題,是因為該問題與人應該如何生活才有意義緊密相關。也就是說,在倫理生活中人們應該遵循怎樣的方式生活才是有意義的。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是倫理道德研究領域不可回避的。誠如威廉斯在《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EthicsandtheLimitsofPhilosophy)中所指出的那樣,“人應該怎樣生活”[4]5。如此一來,德性與幸福的問題便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主題,因為它不僅和人們究竟應該怎么生活相互關聯著,而且還涉及到人們的日常倫理生活問題。當代美德倫理學不再把倫理規范的約束力作為研究的重點,而是從倫理行為者自身的品德或德性出發重新思索倫理問題。義務論倫理學通過把遵守倫理規范行事視為倫理行為者的義務,從義務的角度解釋倫理規范的約束力。這種解釋方法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有其道理,但是僅從義務的角度思考倫理問題還是不夠的。其原因在于,倫理生活中的倫理問題涉及諸方面的因素,它不僅和倫理行為者有關,而且還和各種倫理道德規則聯系密切。這些倫理道德行為規則或準則始終在現實的倫理生活中左右著人們的倫理行為,并且它們還調節著人們相互之間的倫理關系。
由于義務論倫理學過于強調義務的重要性,因此該學派對倫理行為者自身德性方面的研究略顯不足。相反,美德倫理學所突出的正是義務論所忽略的倫理行為者自身的德性因素,并把這種德性作為思考倫理問題的基底。這樣一來,美德倫理學基于德性維度思考倫理問題的做法逐漸被人們接受,該學派在倫理道德領域的重要性也日漸顯著。用邁克爾·斯洛特(MichaelSlote)的話說,在美德倫理學中,“美德起著基礎性作用,而非次要的或衍生性作用;他們通常聚焦于兩個特征,這兩個特征或許能將一門整體性的美德倫理學與康德主義、功利主義和常識直覺主義等那些更為人熟悉的理論區分開來。……美德倫理學將奠基于善好和卓越(及其對立面)的德性論(aretaic)概念,而非諸如‘應該’‘正當’‘錯誤’和‘必須’等道義論(deontic)概念”[5]。可見,美德倫理學有其自身的特點,它也是思考德性與幸福問題的重要路徑。
然而,德性與幸福之間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倫理道德領域探討的重要話題。在具體的倫理生活實踐中,有德性的人是否能夠獲得幸福,或者幸福的人是否是通過德性取得幸福,諸如此類的問題是解釋德性與幸福之間關系的關鍵。換句話說就是,德性與幸福是否具有一致性,“德福一致”有無實現的可能路徑。
二、德性與幸福具有一致性的必然邏輯
德性與幸福的一致性問題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說,以及伊壁鳩魯主義和斯多葛主義的倫理主張。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說中,如果一個有德性的人在現實的生活中過著不幸的生活,那么這個人不能稱之為幸福的。伊壁鳩魯主義從人的本性出發思考倫理問題,并把人的本性視為趨樂避苦的,因此他們把快樂看作幸福,進而將這種快樂的幸福當作德性。與之相反,斯多葛主義則把德性本身視為幸福的,過有德性的生活即是幸福的生活。在當代倫理問題的研究領域中,美德倫理學和規范倫理學都對德性與幸福的一致性問題做出過闡述,只是由于他們各自的哲學立場不同所得出的結論也各有特點。因此,德性與幸福是否有一致性是詮釋德性與幸福之問題的關鍵。
從亞里士多德倫理學說的整體來看,他將幸福解釋為最高的善,但這種最高的善并不是柏拉圖意義上的善之理念,而是和倫理行為者自身的德性相關的善。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解,這種最高的善的實現必然要和現實的倫理生活融為一體,在現實的倫理實踐中獲得幸福。因此幸福作為最高的善本身就包含著實現幸福的質料性因素。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有德性的人過著不幸的生活是不能被稱為幸福的。正如黑格爾所言:“幸福的問題后來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按照亞里士多德,幸福乃是最終目的,乃是善;不過它也是這樣的東西,生存是應當與它相適合的。”[6]380伊壁鳩魯主義則把人的本性視為趨樂避苦的,并在此基礎上將過快樂的生活視為幸福。一方面,在伊壁鳩魯主義那里人追求作為快樂的幸福是其本性使然,而這種幸福和人的德性本性相關,正是基于此伊壁鳩魯主義才“以福為德”;另一方面,對于痛苦的規避也是伊壁鳩魯主義的倫理主張,避免痛苦趨向幸福是人德性本性的體現,因此伊壁鳩魯主義把作為快樂的幸福視為德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伊壁鳩魯主義對德性與幸福一致性問題的觀點是“以福為德”的。與伊壁鳩魯主義的觀點相反,斯多葛主義認為過有德性的生活本身就是幸福的。依據斯多葛主義的解釋,“德性是至善和最大的幸福,因為只有有德性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過這樣的生活就是實現自我;而實現真正的自我,就是為宇宙理性的目的而服務,為宇宙的目的而盡力。這意味著一個博大的社會,其中有理性的人類享受平等的權利,因為理性為人所共有,而一切又同屬于宇宙靈魂”[7]119。在斯多葛主義那里,無德性做不道德的事是最大的惡,這種行為永遠不能獲得幸福。對于幸福而言,人在現實的倫理生活中無需特意追尋,只要作為一個有德性人過有德性的生活,那么幸福自然會降臨,而且這種作為德性的幸福是永恒的。顯然,在對待德性與幸福一致性問題方面,斯多葛主義更傾向于“以德為福”的主張。
然而在斯洛特看來,“伊壁鳩魯主義與斯多葛主義之間如此鮮明而徹底地針鋒相對,這一事實或許能幫助我們發現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非利己主義的美德倫理學有能力以一種像功利主義那樣徹頭徹尾的方式把我們的幾個主要倫理類別統一起來;如果不去思考這兩種古代思想的這種對峙,我們可能就無法發現這種方式”[5]245。這就意味著,伊壁鳩魯主義和斯多葛主義對德性與幸福的倫理思考啟發著當代倫理學的發展,他們關于德性與幸福一致性問題的主張同樣對解釋德性與幸福的問題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盡管,伊壁鳩魯主義與斯多葛主義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當代的不同,但他們的這種倫理思維方式亦然促使人們不斷追尋倫理問題的答案。然而,德性與幸福的一致性問題涉及到倫理生活中的實際因素,它和人們如何選擇倫理生活的方式緊密相聯。因為人作為社會中的成員必然要和其他人打交道,否則孤立的個人將無法在社會中生存。這樣一來,必然會面臨著諸如倫理道德實踐問題,以及如何與他人在倫理生活中和諧相處的問題。換句話說,實現倫理生活中的幸福僅憑個人之力是達不到的,純粹依賴于德性也是行不通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幸福的實現需要倫理生活中的質料性因素作為支撐,它絕不是理論層面的假定與推理。
需要注意的是,德性與幸福一致性的問題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它更關乎于倫理實體和倫理個人之間的關系。如果僅從個人的視角出發思索德性與幸福一致性的問題,那么必然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為在現實的倫理生活中,一個具有德性的人很可能得不到倫理生活中的幸福,相反他可能過著不如沒有德性人的生活。這樣一來,如何解釋這種悖論性的問題便成了倫理道德研究領域所面臨的問題。
相關期刊推薦:《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原《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雙月刊)創刊于1979年,是西華師范大學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注重反映社科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積極追蹤社會學術熱點和理論前沿,所刊論文具有科學性、創新性和實踐性。在編校質量和編排規范上追求高標準、高品位。主要刊載哲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文學、語言學、歷史學、教育學等學科的學術論文,辟有巴蜀文化研究、三國歷史文化研究等。
事實上,人作為倫理實體中的一員,他必然和家庭、社會以及國家等倫理實體息息相關,離開這些倫理實體倫理個人的幸福是無法獲得滿足的,德性與幸福的一致性問題也無法得到解釋。這就表明,倫理實體中的倫理規范或道德規則對于闡釋德性與幸福一致性問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地位。也即是說,思考德性與幸福的一致性問題需要倫理規范或道德規則的基礎,否則德性與幸福的一致性將無法實現,而且也不能有效地說明德性與幸福在倫理生活中的不對等現象。比如,當人們在倫理生活中指責一種行為不符合倫理規范或道德規則時,往往會有不同的情況出現。按照斯洛特的說法,“在重寫‘可指責性的概念∕詞語時,功利主義把它還原為一個更加經驗性的詞語:一個行動的可指責性被重新理解為,存在著一種去指責這一行為的道德義務;而義務的概念又可以進一步地用效用原則來解釋;而‘去指責一個行為與不去指責這一行為相比,能產生更好的后果’這一事實又被最終解釋為‘去指責這個行為與不去指責這個行為相比,將會產生更大的總體快樂(或欲望的滿足)’”[5]210。之所以出現如此局面,是因為一方面倫理問題本身具有復雜性,它所涉及的因素有很多不僅和倫理實體相關,而且還和行為者自身的德性關系密切;另一方面,這些不同的解釋是基于不同的理論立場給出的,由于理論立場相異所以他們所得出的結論必然不同甚至相反。這說明對德性與幸福一致性問題的思考,既不能離開倫理實體也不能忽視倫理行為者自身的特質,否則對該問題的解釋必將是片面的。其實,如果德性作為好品質或卓越才能的含義不能實現出來的話,那么僅擁有這種德性的人是不能稱之為幸福的。當然,若要實現出這種好的品質或卓越才能,就必然需要倫理實體提供條件和機遇,否則只能是空有德性卻無實現它的必要條件。——論文作者:毛華威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