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0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谷苞先生在新疆天山南北的農牧區社會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在前期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谷苞先生在關注絲綢之路的過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思想,進而將其用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多民族關系;同時,谷
摘要: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谷苞先生在新疆天山南北的農牧區社會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在前期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谷苞先生在關注絲綢之路的過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思想,進而將其用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多民族關系;同時,谷苞先生認識到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形成了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是中華民族形成的前提,也是中華民族發展的基礎,這是谷苞先生最重要的民族學研究成果。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增強,并對中華民族進行長時段的形塑。谷苞先生的“中華民族的共同性”理論,在當下具有重要的意義,可以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資源與實踐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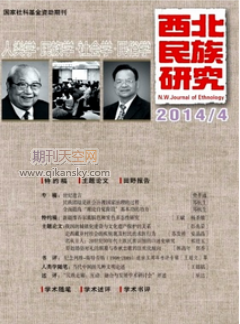
關鍵詞:谷苞;交往交流交融;中華民族的共同性;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如果考察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社會學史,就會發現“魁閣時代”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在抗戰時期,谷苞先生和費孝通、張之毅、田汝康、史國衡、許烺光、李有義、胡慶鈞等諸位先生都是魁閣重鎮的要員。20世紀后半葉,谷苞先生在新疆農牧區社會開展調查,為新疆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從事新疆民族地區社會調查的過程中,谷苞先生的民族學研究思路發生了一定的轉變,他開始涉及新疆多民族歷史的研究。新疆是絲綢之路的核心區,新疆的多民族歷史也是絲綢之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絲綢之路上不同的文化會跨越各種邊界,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共有,絲綢之路最基本的特色是多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通過對新疆多民族歷史與絲綢之路的研究,谷苞先生開始關注中國歷史上多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此基礎上,谷苞先生進一步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共同性”,這是谷苞先生對民族學界的重要貢獻。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當下,谷苞先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思想與“中華民族的共同性”理論對于新時代的民族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作為研究基礎的社會調查
谷苞先生的社會學與民族學研究基本上是以社會調查為基礎展開的,他先后深入中國的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進行調查研究。縱觀1949年之前谷苞先生的社會調查,一方面是對邊政地區的廣泛關注,這也是當時興起的一種風潮;另一方面是對中國農村的深入思考。由于長期在邊區進行社會調查,谷苞先生對甘肅邊區民眾生計問題產生憂慮[1],《為籌邊者憂》[2]是谷苞先生為邊區社會問題發出的一聲吶喊,體現了谷苞先生的憂國憂民情懷。對中國農村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也是20世紀上半葉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以及民國時期一大批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使命。谷苞先生在考察農村問題時,把中國西北農村的癥結歸為借貸問題與土地制度問題。正如張亞輝在分析谷苞先生的卓尼經濟研究時,用“土地制度”與“邊政憂思”總結谷苞先生的研究主題[3]。其實,谷苞先生1949年之前的社會調查完全可以納入二者之中,只是他在研究土地制度的過程中發現了農村的其他問題,如高利貸等,這也體現了谷苞先生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情懷和擔當。
1949年,谷苞先生投筆從戎,穿上軍裝,離開蘭州赴新疆。谷苞先生1950年進入新疆北部的農牧區社會,在伊犁專區鞏哈縣(今尼勒克縣)的蒙古族牧區進行調查,發現階級剝削和壓迫是20世紀50年代之前新疆牧區社會的主要問題[4]320-355。1951年,谷苞先生隨調查組進入新疆南部地區的維吾爾族農村,調查莎車縣四區四鄉,關注南疆維吾爾族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新中國成立前的階級剝削[5]87-102,以及南疆維吾爾族社會的封建集團和政權組織[6]213-221。1958年,進入南疆地區墨玉縣夏合勒克鄉,調研新中國成立前當地的封建莊園和農奴制[7]1-86。除以上調查之外,谷苞先生還在新疆進行過多次調查,單獨或與他人合作完成了一些有重要意義的調查報告。
自1950年以來,谷苞先生在新疆天山南北的農牧區社會作了廣泛的實地調查,正如他自己所說:“解放初期,我的工作、學習的生活基本上是在維吾爾族農村、哈薩克族的牧區度過的。其中,三次到南疆十四個縣的維吾爾族農村進行過社會調查,三次到北疆五個縣的哈薩克族的牧區進行過社會調查,兩次到蒙古(族)牧區進行過社會調查,一次到民族雜居的烏魯木齊市近郊進行過社會調查。”[8]411縱觀20世紀50年代之后谷苞先生在新疆的社會調查,可以發現這些調查部分地承襲了其前期社會調查的脈絡,關注和思考新疆農牧區社會問題的關鍵因素。和以前有所不同的是,這一時間段谷苞先生基本使用階級話語的分析范式,把這種范式置于特定的時代語境之中,也不失為一種有效分析社會問題的路徑。谷苞先生長期以來的社會調查為往后民族問題的思考以及民族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李正元指出:“調查資料是谷苞先生學術研究的資料和觀點來源之一,也是其晚年進行宏觀中華民族問題思考的經驗基礎。”[9]4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華民族共同性生成的基礎與機制
1956年,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成立,谷苞先生擔任副院長。1957年,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歷史研究室成立,谷苞先生兼任歷史研究室主任[10],承擔新疆多民族歷史的研究工作。由于新疆地處古代絲綢之路,古代絲綢之路的很多特色在新疆都有所體現,谷苞先生發現了歷史上絲綢之路的主要特色是文明的互動與交融。在絲綢之路上流動的不同人群,攜帶著各自的物品(商品)和文明,穿梭在中原和西域之間。由此絲綢之路實現了物品(商品)跨地域、跨族群的流通,也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交流。在這種情形之下,絲綢之路上的文化為不同的人群所共享,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了很多相同的成分,同時絲綢之路上流動的文明經常出現相互融合現象。其實,絲綢之路只是反映社會流動與文化傳播的一個窗口而已,歷史上人群的互動與文化的流通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盡管在有些情境下,人們把自己框定在特定的范圍之內,強調特殊性和獨有性,但是文化的共享性誰也無法抵擋。就空間而言,盡管不同的人群之間有一定的距離,相同的文化卻能把他們關聯在一起。就時間來說,不同人群之間的交往與互動早已發生,只不過有時候是一段塵封的歷史而已,很可能在歷史的長河中不同人群之間的互動頻繁發生。
每當談到絲綢之路,物種的流動就成了一個不能避開的重要話題。谷苞先生在考察中原和西域在農作物方面的交流時羅列了歷史上從西域進入中原的一些水果、蔬菜等農作物,并指出:“在說到古代由西域傳入內地的各種農作物的時候,我們便不能不想到,由內地傳入新疆的農作物又是些什么呢?”[11]182緊接著又指出:“至今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對花生、洋芋、茄子、白菜、韭菜、芹菜、辣子等的稱呼,仍然沿用著漢語名稱,就很清楚地說明它們是由內地傳到新疆的。”[11]182農作物在絲綢之路上流通的過程中,種植技術的交流與傳播也在進行。“絲綢之路”的名稱本身就體現出絲綢以及蠶絲生產技術的重要性,基于此,谷苞先生對于養蠶織絹技術從內地傳入新疆的過程進行了論述和分析[12]156-160。
談及絲綢之路上的文化流通,會發覺音樂和舞蹈是一個經常出現的話題。各種文獻中的“胡樂”“胡舞”成為歷史上西域樂舞的代名詞,也見證了中原與西域之間在歷史上的文化交流。谷苞先生關注到歷史上西域與中原之間在音樂舞蹈文化方面的廣泛交流。樂舞文化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過程是比較復雜的,既有東向的傳播,也有西向的流通。谷苞先生分析了古代龜茲樂舞進入中原內地的過程以及在歷史上的流行狀況,強調了西域樂舞對于中原社會的影響,以及西域樂舞在中原地區“在地化”的過程[13]172-177。歷史上的河西走廊是進入西域地區的門戶。由于地緣關系,哈密盆地與河西走廊之間的文化交流比較普遍。谷苞先生關注過歷史上的伊州(哈密及周邊地區)與河西走廊之間在音樂文化方面的交流,通過對《伊州樂》與《涼州樂》的比較分析,發現了二者的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融合了龜茲樂舞、漢族音樂文化與當地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14]。這一點,也是絲綢之路研究領域近年來關注的熱點。在絲綢之路的研究中,一般認為獅子是古代絲綢之路上流通的物種,經歷了從西域進入中原的過程。而獅子舞是一種在絲綢之路上流行的藝術,谷苞先生對曾經在中原地區廣為流行的獅子舞進行了分析考證,指出獅子舞從波斯傳入龜茲,再由龜茲進入內地[15]73-82。樂器是樂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同區域樂舞文化的交流必然意味著樂器之間的交流,谷苞先生也注意到這一點。在關于鼓吹樂的論述中,他指出北方游牧民族的樂器及音樂文化首先傳入內地,形成了鼓吹樂,然后內地的鼓吹樂又傳到北方游牧民族地區[16]100-112。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文化的交流是常態,樂舞文化僅為一種交流的案例類型。
相關期刊推薦:《西北民族研究》1984年試刊,創刊于1986年。刊發蒙古學、藏學、阿爾泰學、中亞、回族伊斯蘭以及敦煌學、西夏學、絲綢之路等領域之人類學/民族學、民族社會學、民俗學方向的專業研究與田野考察的論文、報告。涉及歷史、宗教、語言文字、文化藝術等等領域。本刊嚴格編風、嚴格學術規范、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操作、培養學術新人的舉措等等。獲得學者、讀者好評。
河西走廊歷來是一個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帶,在這條多民族走廊內部曾演繹過一些多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這一點谷苞先生在研究中有所關注,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就涉及歷史上河西走廊與西域之間樂舞的交流交融過程。自西漢以來,隨著河西四郡的設置,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天山北部地區這三個大游牧區的邊緣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農耕社會,同時商業也開始在河西走廊的農耕區域內部興起。從此,河西走廊在王朝國家時期的戰略意義更加突出,一方面起到隔斷羌胡的作用,另一方面對于中國早期疆域的形成與鞏固以及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具有重要意義。谷苞先生強調了河西四郡的設置對于關聯周邊幾大農業區與游牧區的意義[17]。河西走廊對于周邊游牧區域的部分民族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因為當地能夠為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天山一帶游牧區的部分民眾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大量物品,這就促成了河西走廊與周邊地區的交往交流,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在探討河西走廊的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關系的基礎上,谷苞先生進一步總結了西北地區的漢族農業區與少數民族游牧區的關聯。谷苞先生指出:“在歷史上,西北地區一直是我國主要牧區的所在地,由于游牧區的少數民族牧民不能生產自己所需的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需要漢族農業區為他們提供糧食、各種金屬工具、絲、麻等衣著材料、茶葉、瓷器等等。農業區的漢族居民也很需要游牧區的牲畜及各種畜產品。在這方面漢族農業區與少數民族的游牧區長期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18]143-144
盡管在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出現過沖突和戰爭,但多民族關系的主線還是交往交流。歷史上交往交流是各民族群眾日常生活的主題,隨時隨地都在發生,而民族之間的沖突和戰爭經常與政治關聯在一起。由于歷史書寫與歷史講述的緣故,長期以來人們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在民族關系的天平上,砝碼總是有意無意地向沖突及戰爭的一端傾斜,而忽視了作為主流關系的交往交流。關于這一點,谷苞先生在論析中指出:“我們認為:在歷史上我國民族關系的主流為我國各族人民群眾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19]谷苞先生在論述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關系時進一步論述:“農業區與游牧區的并存,兩者之間的戰爭,特別是游牧民族中的統治階級(奴隸主與封建主階級)所發動的掠劫性的戰爭雖然史不絕書,但這不是農業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民族關系的主流;兩者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密切聯系,以及從而產生的兩者之間在經濟上互相依存、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才是歷史的主流。”[20]7
西北地區的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在交往交流的過程中,不同民族之間的融合現象時有發生。在多民族的互動交流中,或是農耕民族融入周邊的游牧社會,或是游牧民族融入農耕民族。農耕區域的一些漢族民眾為了生存進入周邊的牧區社會,到了下一代基本上完全融入游牧民族之中。這種個體化的融入,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當然融入是雙向的,由于各種原因,也有部分游牧民族融入農耕社會。在農耕和游牧過渡帶上的部分族群,到底發生了少數民族的漢化還是漢族的少數民族化?在有些情況下,歷史事實與現實認同可能會有一定的錯位。谷苞先生于20世紀40年代在洮岷走廊的漢藏交界地帶調查時就已經發現了這一問題,并且指出:“我們訪問遇到洮河上游的許多番村和番民家庭,他們中很多都有漢族的血統。一般旅行過這些地方的人士,都曾注意到一個事實——番民的漢化,可是他們卻忽略了另一個事實——漢族的番化”。[21]中國歷史上多民族之間的交融是一種常態,而且交融是多向的,根據具體的歷史情境,不同民族之間的交融時有發生。谷苞先生分析了歷史上多民族交融的類型,指出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融合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有大量的少數民族融合于漢族之中;二是有大量的漢族融合于少數民族之中;三是各少數民族相互融合[22]。在一個多民族地區,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中華民族就是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
三、“中華民族的共同性”理論闡述
關于中華民族的共同性的研究,是谷苞先生學術思想的精髓。20世紀80年代中期,谷苞先生發表《論中華民族的共同性》(1985年)和《再論中華民族的共同性》(1986年)兩篇論文;2007年,谷苞先生又發表了《三論中華民族的共同性》。這三篇文章相繼闡述了“中華民族的共同性”理論。谷苞先生的觀點在當時得到費孝通先生的贊同和支持,前兩篇論文收入費孝通先生主編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書中[23]132-165。當然,在谷苞先生的其他論文中也有一些關于中華民族的共同性的具體論述與思想表達。谷苞先生的“中華民族的共同性”理論,不僅在當時的民族理論與民族實踐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顧頡剛先生于1939年在《益世報·邊疆周刊(第9期)》上發表了《中華民族是一個》[24]34-44,然后學界圍繞“中華民族是一個”展開了大討論[25]。隨著中國民族識別工作的進行以及注重追溯源流的族別研究的興起,在民族學界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研究單一民族的成果居多,而研究多民族關系的成果相對要少。針對當時的民族學研究現狀,谷苞先生也看出了單一民族研究的理論范式對于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和制約,于是開始對中華民族的共同性進行探索。他在《論中華民族的共同性》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國境內有五十六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著各自的族名,同時,五十六個民族又有一個共同的族名,即中華民族。”[26]在界定“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的同時,谷苞先生對“中華民族的共同性”作了界定:“在長期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生活在中國領土上的漢族和各少數民族,都有著各自所獨有的鮮明的民族特點與特長,同時又有著許多民族所共有的共同之點,即中華民族的共同性。”[26]
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是中華民族形成的前提,更是中華民族發展的基礎。中華民族的共同性的核心就是文化,其內涵包括諸多的層面。就中華民族的共同性來說,語言及以語言為載體的口頭傳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語言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語言也反映了文化的特征。關于民族和語言之間的關系探討,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正如谷苞先生指出的:“在我國,有些民族共同使用著一種語言文字,有些民族主要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有些民族沒有文字,使用本民族的語言,使用其他民族的文字,其中最主要的是使用漢文;有些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語言外,還同時使用一種或幾種其他民族的語言。”[26]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語言既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又存在著相同性。一方面,這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眾之間互動交流的結果;另一方面,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眾在互動過程中,總會把某一種語言作為雙方或多方交流的共同語言。在很多情況下,歷史上多民族的互動會把漢語作為共同的交流語言,當然在有些情況下也會把某一種少數民族語言作為交流的共同語言。關于這一點,谷苞先生指出:“在這方面存在著兩個特點:一個是全國性的特點,有許多少數民族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能使用漢語、漢文,也有一些少數民族通用漢語、漢文;另一個是地區性的特點,如在五個自治區和甘肅、青海、云南、貴州等多民族的省內的人數更少的少數民族,都分別能使用蒙語、維語、藏語、僮語、苗語、彝語等。在我國語言使用上,既存在著多民族的特點,又存在著中華民族的共同性。”[26]長期以來,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過程中,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逐漸生成,這恰恰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性的一個重要體現。——論文作者:李建宗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