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3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在有關社會發展問題的早期研究中,青年恩格斯而非青年馬克思,扮演了思想啟發者的角色。正如早期新聞作品所展示的,青年馬克思更加關注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窘境,而青年恩格斯更早地注意到掙扎在工業化中的產業工人。不僅如此,青年恩格
摘要:在有關社會發展問題的早期研究中,青年恩格斯而非青年馬克思,扮演了思想啟發者的角色。正如早期新聞作品所展示的,青年馬克思更加關注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窘境,而青年恩格斯更早地注意到掙扎在“工業化”中的產業工人。不僅如此,青年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揭示出資本邏輯的起點是私有制,這一發現對青年馬克思同時期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后期的《資本論》都產生過深刻影響,尤其是強化了青年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回應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分析路徑。此外,青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側重“社會觀察”和“經驗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的方式,為當時側重以抽象論證針砭時弊的青年馬克思帶來新視角,從而使二人共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煉出社會發展理論的“現實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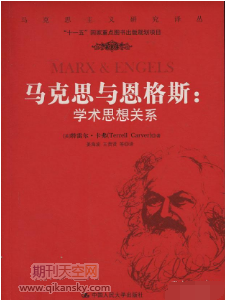
關鍵詞:青年馬克思;青年恩格斯;學術關系;社會發展思想
法國哲學家薩特曾認為恩格斯曲解了馬克思的觀點[1]。事實上,有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術思想關系的討論從未停止。迄今為止,這場討論仍未形成任何明顯共識。近年有關這一主題的研究,可概述為三個不同的理論陣營:其一為“對立論”,即堅持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存在重大差異,代表人物主要包括諾曼·萊文[2]、戴維·麥克萊倫[3]等在內的一些西方學者;其二為“一致論”,即傾向于認為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完美合作者,并且在重大問題上秉持一致的觀點,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包括朱傳棨先生的《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比較研究》[4]、亨利的《恩格斯的生活與思想:一個重新解釋》[5]等;其三為“差異論”,這類學說的立場較為溫和且具有轉換性,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時期的思想應當得到不同的分析與考量,其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包括特雷爾·卡弗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思想關系》、俞吾金先生的《問題域的轉換》[6]等。事實上,由于以上三個理論陣營在“時間跨度”(究竟以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青年時代或成熟時期亦或二者的整體學術生涯作為標準)和“具體主題”這兩個關鍵事項的選取上并不一致,所以,其達成的結論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現巨大的分歧。鑒于此,本文將通過限定“時間跨度”(1839-1846)和“具體主題”(社會發展思想),將馬克思與恩格斯之學術思想關系的考察以更為細致且具體的方式呈現,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為解決上述爭論提供新的契機。
一、產業工人:現代社會結構中的“中流砥柱”
眾所周知,青年馬克思與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11月的第一次會面并不愉快。那時,青年恩格斯已多次在公開刊物上發表作品,并曾向《萊茵報》投稿。青年馬克思也已發表多篇文章,并擔任《萊茵報》主編。然而,當時更為擁護“自由人派”的青年馬克思認為,與“青年黑格爾派”互動密切的青年恩格斯與他并無太多思想共識。因此,在第一次會面之后,二人并未即刻開啟日后令人稱羨的良好合作關系。
青年馬克思雖然初期并不認為青年恩格斯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但是從未拒收恩格斯來自英國的投稿。恰恰相反,《萊茵報》多次發表恩格斯的稿件。這一事實說明,一方面,青年恩格斯在其早期新聞作品中表達的政治興趣和敏銳洞察力與青年馬克思極其相近。另一方面,青年恩格斯能夠提供當時在德國的青年馬克思不能完整收集的英國實證材料。以上兩個方面,為他們二人能夠在后期形成良好且持久的合作關系打下了重要基礎。
回顧二人早期的新聞作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時代,均對當時政治環境中受到限制的新聞自由表達過強烈不滿。1841年12月,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頒布實施。1842年初,青年馬克思撰寫系列文章論述時事的計劃,在“書報檢查令”約束之下,只有《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和《摩塞爾記者的辯護》等幾篇文章得以見報。同一時期,青年恩格斯的許多文章,源于相似原因而不能付諸印刷。青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不懈地撰寫文章表達見解,并投身與時政相關的辯論中。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1842年5月)中,馬克思認為,書報檢查令無法促進新聞自由,只會成為桎梏思想進步的壁壘[7]。同一時期,在1842年7月《普魯士新聞出版法批判》的評論中,恩格斯表述自己對“書報檢查令”諸多法條的不同意見,期望以此表達群眾對國家機構非自由主義陳腐行為的反感和抗爭[8]472。
不僅如此,青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作品中均對當時社會的弱勢群體表達了高度關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歐洲大陸,在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下,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城市與農村、商業與農業、富人與窮人,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分化,社會結構日益復雜。青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在復雜勢力的角逐中,階級的分化與對立日益明顯。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和《摩塞爾記者的辯護》等文章中,馬克思譴責當時既得利益群體只關注自身利益得失,而無視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需要。馬克思指出,這些既得利益者試圖通過法令和行政等方式毀滅社會弱勢群體獲得利益配額的可能性,他們意圖固化社會結構而粉碎社會弱勢群體改變困境的嘗試。同一時期,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的《伍珀河谷來信》中直陳工業地區工人的生活窘境。恩格斯指出,在工業地區的上空充斥著揮之不去的疲憊、混亂、反理性,以及蒙昧氣息,在谷區工人的壓抑生活之中再不可見健康與朝氣[8]43-44。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對“弱勢群體”的共同關注中,商業出身的青年恩格斯比學院出身的青年馬克思更早注意到“產業工人”及其在現代階級結構中的重要地位。青年恩格斯言及的伍珀河谷地區,是當時普魯士的工業化區域。19世紀40年代,這一地區開始呈現工業化進程的諸多弊端,例如,低效的政府、正統教義的統治、工業的污染、工人的貧困,等等。盡管未能接受正規大學教育,但是,早已接觸家族產業的青年恩格斯直接參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商業活動。基于這樣的成長經歷和自身的敏銳洞察力,青年恩格斯發現在資本主義迅速崛起所帶來的復雜社會環境中產業工人的糟糕境況。與此同時,取得博士學位后即在報社工作的青年馬克思,顯然更多地關注當時更具時政意義的事件。尤為重要的是,青年馬克思在理論介入時政事件之時,更為關注農民、種植園主、小手工業者等弱勢群體,而非青年恩格斯在《伍珀河谷來信》中提到的產業工人。毋庸置疑,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行程脈絡而言,產業工人才是理解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之內在問題的關鍵,也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后期研究的關注重點。
如上所述,雖然青年馬克思與恩格斯早期的理論側重點不盡相同,但這并不構成阻斷二人日后合作的障礙。毋寧說,共同的政治興趣和社會觀察視角,成為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之學術合作關系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礎。基于對弱勢群體的共同關注和社會觀察視角,青年馬克思以系統的理論解析小手工業者、農民與資產階級及土地所有者之間的沖突,青年恩格斯以產業工人的窘迫現狀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結合二人后續的研究脈絡,產業工人相較于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承載與反映更多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問題。因此,從這一角度而言,青年恩格斯比青年馬克思更早發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關鍵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青年馬克思將當時研究重心轉向產業工人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理論(包括階級結構理論)。
二、政治經濟學批判:解決現代社會問題的新路徑
1843年3月末,《萊茵報》被迫停刊,青年馬克思、阿諾德·盧格以及莫澤斯·赫斯計劃在德國以外創辦新的刊物,以繼續他們在《萊茵報》未完成的批判事業。同年11月,《德法年鑒》收到青年恩格斯的投稿《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①。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卡弗教授指出,青年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對政治經濟學的闡釋,顯然比20年前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揭示的市民社會政治生活的虛偽更加犀利[9]36。在這篇被馬克思譽為“天才大綱”[10]592的投稿中,青年恩格斯揭露國民經濟學家的偽善以及他們避而不談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前提,更進一步指出資產階級社會不可避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這一作品促成馬克思從前期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中抽離,走向后期研究中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下文將具體闡釋此時的恩格斯如何影響了馬克思,尤其是如何啟發青年馬克思逐步轉向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路徑來解析社會問題。
在國民經濟學家的語境中,國民經濟學是研究如何促使國家強盛和國民富裕的科學。然而,在青年恩格斯看來,“國民經濟學的產生是商業擴展的自然結果,隨著它的出現,一個成熟的允許欺詐的體系,一門完整的發財致富的科學代替了簡單的不科學的生意經”[11]56。國民經濟學家宣稱自己的理論是進步的、友善的、公平的,甚至是“各民族、各個人之間的友誼和團結的紐帶”;但是,青年恩格斯明確指出,“這種理論是迄今存在過的體系中最粗陋最野蠻的體系”,它的存在否定了“關于仁愛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詞”,它創造和發展了殘酷性與古代奴隸制度相比并不遜色的“工廠制度和現代的奴隸制度”[11]58。
相關知識推薦:論文重復率0好發表嗎
在國民經濟學家的解讀之中,“商品的生產費用由以下三個要素組成:生產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資本及其利潤,生產和加工所需要的勞動的報酬”,而且在他們看來“資本和勞動是同一個東西”[11]67。按照這種解讀,生產就只包括兩個方面,即客觀的土地和主觀的人的勞動。與之不同,青年恩格斯認為,生產的主體性“還包括他的肉體活動和精神活動”,而且,列入生產要素的精神要素應該“在經濟學的生產費用項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11]67。青年恩格斯進一步指出,那些看似更為先進的、距離他們所處時代更近的經濟學家更加偽善,因為他們更擅長運用有技巧的詭辯遮掩其所處時代的殘酷現實,正所謂“李嘉圖的罪過比亞當·斯密大,而麥克庫洛赫和穆勒的罪過又比李嘉圖大”[11]59。
更為重要的是,青年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揭示了被國民經濟學家的偽善所刻意回避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前提問題,即“私有制的合理性”問題。事實上,有關這一問題的反思,也成為馬克思后來撰寫《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關鍵所在。青年恩格斯率先從經濟活動的現實出發,創造性地指出資產階級社會(商業社會)中的無休無止“競爭”的根源是“私有制”,這才是資本邏輯的開端,也是國民經濟學家刻意回避的重要前提。青年恩格斯犀利地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終究會歸結為競爭。”[11]72換言之,競爭只是表象,只是私有制的結果,并不構成資本邏輯的起點。只不過,過度的競爭狀態使得身處其中的勞動者、資本所有者甚至國民經濟學家都感到茫然無措。“資本對資本、勞動對勞動、土地對土地的斗爭,使生產陷于高燒狀態,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關系都顛倒過來。”[11]76-77同時,在青年恩格斯看來,無限擴張的“競爭”遵循一定的規律。“競爭的規律是:需求和供給始終力圖互相適應,而正因為如此,從未有過互相適應。雙方又重新脫節并轉化為尖銳的對立。”[11]73-74然而,競爭的規律是“一種達不到目的的永恒波動”[11]74,由競爭關系所造成的價格的永恒波動使得“商業完全喪失了道德的最后一點痕跡”[11]75。
至此,青年恩格斯完成從商業社會具體經濟活動出發對國民經濟學家的批判,指出資產階級社會的前提,反思商業社會的現狀和矛盾,并延伸至價值理論的國民經濟學批判。雖然恩格斯最終關于經濟體系的論述,尤其是價值理論的論證更多地圍繞“價格”而不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關系”,但是,這并不妨礙馬克思在同時期《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后期的《資本論》中多次引用青年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此外,青年恩格斯在這一作品中將生產要素定性為“自然與人”的思考,也成為馬克思批判拉薩爾派的重要線索。青年恩格斯對“地租”、“資本及其利潤”、“勞動的報酬”的分析,也成為青年馬克思在同時期《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討論“地租”、資本的利潤以及“工資”的重要參照[11]115-155。
如上所述,青年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撕去國民經濟學家的偽善面紗,從道德和經濟學雙重角度批判國民經濟學。無論是作品中的批判對象(國民經濟學家),或是青年恩格斯認定的關鍵問題(私有制的合理性),亦或是他解析問題的方法(社會觀察和現狀分析),都對同時期及后來的馬克思產生有跡可循的積極影響。不可否認,青年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展現的天才洞見和敏銳觀察力,深深地吸引了青年馬克思,二人從此確立正式且友好的合作關系。此外,青年恩格斯拒絕任何黑格爾式先驗的邏輯預設,發掘政治經濟現象的背后原因而探尋社會發展的思路,以及堅持經驗分析基礎上的研究方法,更加堅定了青年馬克思走以政治經濟學批判解構社會問題的新道路。——論文作者:張萌,李志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