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19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進入20世紀以后,東西方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產生了不同的有益于自身的發展和表現。馬克思主義的形象在東西方呈現出不一樣的兩種狀態,在東方是以一種政治手段、政治家的身份站在舞臺中央,而在西方則猶如一把鋼刀毫不留情地刺破資本主義的偽善
【摘要】進入20世紀以后,東西方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產生了不同的有益于自身的發展和表現。馬克思主義的形象在東西方呈現出不一樣的兩種狀態,在東方是以一種政治手段、政治家的身份站在舞臺中央,而在西方則猶如一把鋼刀毫不留情地刺破資本主義的偽善面具。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以霍克海默為首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發展下,開始注重對現實問題的解決,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社會也在遇到問題的同時進行自我的修正和調和,使得馬克思所預想的資本主義將面臨的有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其中所面臨著理論層面的問題與現實層面的問題,其次進行解決的關鍵不是馬克思主義是否依舊適用于對當下社會的批判,而其側重點在于解決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核心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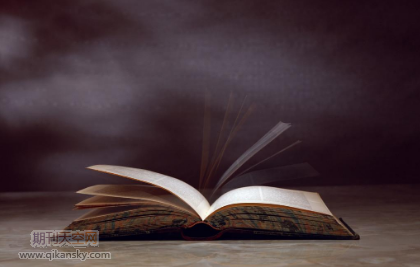
【關鍵詞】哲學;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啟蒙辯證法
資本主義的自我革新以后,使得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高福利的環境下,有效地減少和降低了其資本主義國家本身內在遇到的因矛盾的對立與激化而產生的各種沖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就此失去了應有的批判作用,資本主義以及資本貪婪的本性是絲毫沒有改變的。
一、文明
《啟蒙辯證法》中的啟蒙與理性的邏輯是啟蒙與理性的批判,霍克海默斥責“啟蒙退化為神話,被徹底啟蒙的世界陷入了野蠻狀態”[1]。其中的邏輯是從文明、啟蒙和理性三者進行逐步依次實踐的。從啟蒙運動開始,人們就開始用文明來對抗自然,從啟蒙時代開始,文化概念就包含了文明的要素,正如弗洛伊德所表述的“我們被稱之為文明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們的痛苦”。使得弗洛伊德開始重新審視人類對文明所抱有的種種不滿,霍克海默在此基礎之上繼承發展了此觀點,在《反猶主義要素:啟蒙的界限》一文中,他將現實與自然、文明與屠殺聯系在了一起,在文明發展的同時,伴隨著反猶教主義的屠殺行為。人類社會的現象之中也與對抗自然的勝利是緊密相連的。權杖上的每一顆珍珠都是流著血的,他將極權主義與文明歸為同列,并為同行,其極權主義制度機制如同文明的發展一樣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在此文中,他將文明一詞披上了偽善、消極、貶義的外衣來進行使用。將文明作為一條鎖鏈,來連接多個不同的民族文化。人類發展之始到現在進程的演變,期間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能看見文化的傳播與創造的身影。而這其中也有習俗規范等物質文明的成果。啟蒙運動以后,文化變成了商場貨架上的商品,它可以像信息那樣隨著風與人們的觀念到處傳播,而不再是只留存在尋求他的人中間進行彌漫。同時,思想成了孤立化的探索,一方面將它作為批判固有文化的立足點,另一方面將本身作為批判的對象。
二、啟蒙
啟蒙在反抗權威的過程中,逐步使自己成了權威,大眾文化毋寧是這樣權威之下的產物,康德認為啟蒙“就是人類掙脫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被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2]康德認為人類成就必須是引導啟蒙人類心靈再獨立和運用理智的勇氣都是來自啟蒙,但在人類的發展史上,啟蒙帶來的不光是上述的內容,還有專制統治和殺戮。
啟蒙的出現通常伴隨著科技的進步,啟蒙與神話的辯證關系之中,啟蒙從一開始就用人類所理解和使用的自然科學去消除由神話所帶來的人類被蒙蔽的愚昧,但隨著啟蒙在歷史中不斷地被授予本屬于神話的權利,并在當中代替了神話,使得自己成了權威,人類卻又將自己深深地陷入了沒有目標的野蠻狀態之中,即為啟蒙倒退成為了之前的神話,啟蒙的倒退帶來的是科技對人們的控制和人們對自然的壓制,這樣的表述表明了真正所謂的啟蒙還未降臨,霍克海默在此指出掌握著自身并發揮著力量的啟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啟蒙界限的。因此,啟蒙本身就包含著啟蒙自身對立面。他是具有矛盾的雙重性。啟蒙有兩重含義,第一重含義,是在歷史過程之中被稱之為進步精神,啟蒙是無盡頭、并永遠在進程之中的。第二重含義,具有和神話一樣的有權威性的重要性文化。啟蒙確立了人類在自我單方面的對自然的統治,在此時,啟蒙則完成了啟蒙自身的目的。世界由此也籠罩在啟蒙所帶來的災害之中,正是因為啟蒙的雙重性,才使得文化在歷史進程的不斷發展之中,發生了自身的分裂與矛盾,所確立的原則和規范又反作用于文化自身,使得文化限制了自身的發展,因此啟蒙內在的雙重性的相互對立,這本質上是文明與文化的互相對立。啟蒙思想最開始是本著消除迷信神話的,但真正啟蒙之后的世界,啟蒙坐在王座上卻又變本加厲,反過來壓制人類。此時啟蒙早已與人們設想的相左,此時的啟蒙不再追尋自由,而是毫無保留的控制人類,有規律、有計劃、按照設想的去排除異己。
相關知識推薦:怎么評文學方向的副高級職稱
因為啟蒙所具有的極權性,注定啟蒙不會止步于此,啟蒙占據權威地位后,會使得科學、藝術等都為這個世界的某些特定的需要而服務,不再具有自身對時代的反思。“完全被啟蒙的人”[3]實則應是要被重新啟蒙的個體。霍克海默從始至終都確信,人類可以通過啟蒙并憑借于此進而對自身進行批判,人類可以調和好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最終可以實現揚棄自身,進而實現第一層含義的啟蒙。
霍克海默所提出的啟蒙文化批判的立足點是在于啟蒙與神話的辯證關系,在文中“神話就是啟蒙,而啟蒙卻倒退成了神話”[4]這種表述,用了雙重意義方面中的啟蒙概念,在啟蒙的自由性上進行批判的同時,又對啟蒙的極權性進行了批判,盡管啟蒙辯證法成熟于二戰時期,對至今當下的種種問題依然是一種警示,這其中也是同為批判的實質在其批判的根源。至此,霍克海默表明,啟蒙批判的內涵是理性批判,是人類在發展過程中通過理性闡述的啟蒙。俄狄浦斯對斯芬克斯之謎的解答“這就是人!”[5]——便是啟蒙精神的不變原型。在此事中可以看出人類自始至終是從自身的角度去思考外界的,理性是人類的一種趨向的方向。那是外界所不能自發而形成的,因此人類的發展不斷地在向理性方向發展,所以霍格海默將理性作為考察文化批判的核心。
三、理性
《啟蒙辯證法》將啟蒙解釋為由理性所激發出來的,但這種由理性而引導的啟蒙,未來的何去何從,也順勢成了他所擔心的問題,當“神話變成了啟蒙,自然則變成了純粹的客觀性,人類為其權力而膨脹,付出了他們的行使權力過程中不斷異化的代價,啟蒙對待萬物,就像獨裁者對待人。”[6]在理性趨勢之下,啟蒙占據了曾經神話的位置,這也會使得理性最終完成為了手段,被用于現代科技之中,猶如神話運用文化而為自身服務一樣,霍克海默發現了大眾對文化的接受,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實質依然是被操控著。
在《啟蒙辯證法》中,霍克海默著重地進行了解釋。啟蒙的事業最終成了理性的主體。在這樣一個沒有時間節點的自我保存事業之中,以理性事業為己任的啟蒙卻是在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之后才形成完善的。新教之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后得以確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與傳統的天主教是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將信仰從僧侶手中拿走,并遞給了個人,不再相信神職、僧侶,對神的旨意的傳達,認為人們可以直接同上帝對話,由此,啟蒙將人放在了首要,以人的理性支撐著人類的主體性。
進入現代社會以后,理性由啟蒙占據了主體性的向上發展的道路,成了“普遍大寫的理性”,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驅動下,使得理性發生了變化,不再作為人類安身立命的手段,而是成了守護公序良俗的工具,人與人之間用來約束和管理的工具,成了純粹的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在其功能的轉變下,產生了與之相反的作用。在當下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過程中,人被分為兩類,一是資本所有者;一是勞動力的持有者。都是以自己生活為主體,對資本所有者而言,他的每次行為都由自己選擇而決定,這里的行為是為資本增加,對于勞動者而言,他也在時刻為自己的生活做選擇,并沒有受到他人的指使和奴役。
這種理性操控人們所做出選擇的結果,并不是人們為之努力與神話反抗而得到的。但它又確確實實地出現在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似自由而卻無時無刻不在枷鎖之中。對這種啟蒙后的現代,啟蒙在運用理性的同時,也需要自我反思。這樣才能防止理性如同神話那樣去奴役人類。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中所擔心的,所恐懼的,所不安的并不是啟蒙與神話的關系,而是理性在沒有了拐杖后,是否真的不是一只逃脫了鐵籠的野獸。
霍克海默所批判理性在于,他認為科學是無法涵蓋所有的事物,范疇哲學無法理解所有個體的多樣性,科學最終還是有邊界的,理性亦然也是有邊界的。最后用一句諺語結尾,“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在理性發展為主導的今天,給感性留一塊自留地。——論文作者:趙彧博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