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9-07-04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未來人會敬畏水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這二者的哲學關系從起點歷經(jīng)愛恨相殺又回到起點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同是敬畏,卻有本質(zhì)的不同。前一個是因為無知才不得不敬畏,后一個則是因為有知主動的去敬畏。 【關鍵詞】歷史演進;治水;水患;思想脈絡;敬畏 1
【摘要】未來“人”會敬畏“水”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這二者的哲學關系從起點歷經(jīng)愛恨相殺又回到起點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同是敬畏,卻有本質(zhì)的不同。前一個是因為無知才不得不敬畏,后一個則是因為“有知”主動的去敬畏。
【關鍵詞】歷史演進;治水;水患;思想脈絡;敬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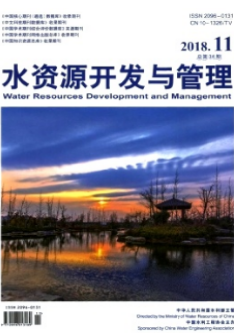
1對“水”的認識的哲學范疇
自從人類中有了哲學,或者有了真正意義的哲學家以來,人對“水”的哲學認識貫穿二條主線,其一是對“水”本身的本質(zhì)認識;其二則是對“人”與“水”的關系的認識。對“水”的本質(zhì)認識,雖然冠以認識,但其實質(zhì)并不在認識二字,而在本質(zhì)。即人的“認識”最終還原到了“水”的本質(zhì),這是一個漫長的逐漸廓清的過程。下面還要具體講到。如果把對“水”本身的本質(zhì)認識比做早夭的孩童,那么“人”與“水”的關系”的認識則壽與天齊,隨著人類歷史會一直延續(xù)下去。
在這條主線中,“人”和“水”從哲學上講是平等的,都是自然界里眾多成員中的一員,不存在著從屬和仆隸關系。兩者又互為主客體,譬如隨著水環(huán)境在內(nèi)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我國癌癥等病癥近些年已由少發(fā)病發(fā)展成了常見病。這即是“人”在使“水”在內(nèi)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患上“癌癥”后反作用于人的生動例證。人與“水”的關系中,有二層意思。其一,人作為一種生物,生理上主要是由“水”組成的,水構(gòu)成了人這個生命體的最重要的內(nèi)環(huán)境。水在人體中所占比重從嬰兒的80%以上到老年50%左右,人的生命逐漸老化的過程也是水的比重逐漸降低的過程。同樣,水也是人最重要的外部環(huán)境之一,可以說,水是人最重要的生存要素。其二,人與外環(huán)境中水的關系,隨著人的認識的增長,經(jīng)歷了一個長期演化的過程。
2對“水“本質(zhì)認識的歷史演進
中國最早的關于水的可靠哲學論述應該是《管子.水地篇》:水者,萬物之本源也,諸生之宗室也!又說“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稍晚的古希臘哲學始祖泰利斯也認為“水是萬物的本原”。這也許并不是巧合,東西方文明在哲學認識上實現(xiàn)了第一次交匯,即“水”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哲學命題和“世界本源”。其后,中國和希臘的哲學進一步發(fā)育,如中國的《尚書·洪范》中有最早的五行學說記載:一曰水,二曰火,三日木,四曰金,五日土,其中把“水”作為構(gòu)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和運動方式。古希臘的恩培多克勒和后來的斯多亞學派亦把水作為萬物的根或基本元素。十七世紀的卡文迪許發(fā)現(xiàn)了“水”僅僅只是化學元素組成的一種化合物。
自然的,以“水”的本質(zhì)為哲學命題進行的研究走到了終點,但是關于人與水之間的關系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哲學命題。另外,在對“水”進行描述時,哲學家們常把水和人的品行相類喻,如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老子說:“上善若水”又說,“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這也可看作的人對“水”認識的題外花絮。
3人與“水“哲學關系的歷史演進
通過人與“水“哲學關系認識的歷史演進過程,我們可以更直觀的了解人與“水“哲學關系的變遷發(fā)展脈胳。我們知道,在遠古荒蠻時代,曾經(jīng)“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大多數(shù)民族傳說都與治水或水患有關,中國“大禹治水”、西方“諾亞方舟”、兩河流域的“吉爾伽美什”。雖然故事的具體情節(jié)有所不同,但都含有英雄平息或逃避水患、拯救部落的主線。這些故事真?zhèn)我巡恢匾瑢嶋H上都隱喻了人類是在戰(zhàn)勝洪水這一可怕的災難后,猶如鳳凰涅磐,從蒙昧邁向了文明。人類從茹毛飲血的原始部落邁向真正的人類社會的過程就是人類戰(zhàn)勝洪水的英雄史詩,從此也就有了真正的人類歷史。
遠古文明都是與“水”息息相關的。我們知道,人類四大古代文明實質(zhì)上都是農(nóng)耕文明,或者可以說是河流文明、“水”的文明。每一個文明背后都有一條或二條哺育人類的河流。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干脆以河流的名稱命名古代文明,如尼羅河文明、黃河文明、印度河文明等。這些河流在給人類帶來洪澇災害的同時,更保證了人的繁衍生息。中國最早的可信治水的應該是《管子.度地篇》,除五害,以水為始”。又說:“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
五害已除,人乃可治”。稍晚有個西門豹治鄴的故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思想脈絡:一是當時人們認為洪水是超自然的神靈施法,人們惶恐無助,只能祈禳以求寬宥;二是西門豹卻敢于忤逆神靈,最后建引漳十二渠造福百姓。到了孔子時則言“災異述天道,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把洪澇等自然現(xiàn)象解釋為上天懲戒和警示人類社會的方式和手段。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說“甚戰(zhàn),水之為利害也”,“自是之后,用事者爭言水利”。
他指出了水與人類生存之間的關系,分析了水的有利與為害的兩個方面,在中國歷史上首次給予“水利”一詞以興利除害的完整概念。由先秦而漢,中國哲學實現(xiàn)儒家學派主導和統(tǒng)治,如果說先前的既有入世之學,又有出世之學,那么此時中國顯學已然已是入世之學,其他學派或湮沒,或隱學。這時,中國哲學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陰陽五行學說”成型,“天人合一”轉(zhuǎn)為“天人感應”。認為只有皇帝“允恭克讓”、“克明俊德”,才能使災異芟除。也就是說,旱澇等天災與皇帝的不端品行有關,這是自然世界與人的精神的關聯(lián)。
到了中世紀,世界哲學有了顯著分野。判斷的重要依據(jù)就是神權和俗權的關系。中國的俗權與神權得到了高度的統(tǒng)一,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所謂“君權神授”,皇帝作為“天子”,代上天的意志行事。這說明,中國哲學已然成為世俗世界的犬儒。即便有張載、王充等人及佛道等出世之學,也只能是旁枝末節(jié),而非主干巨流。對自然哲學的理解更多的是依附與服務于神權和人本身的人格和道德。“格自然之理”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以便“入于圣賢之域”。
因此,也就陷入了理學的窠臼中無法自拔。伊斯蘭教國家神權和俗權則更加緊密,甚爾一體。“哈里發(fā)”既是精神領袖,又是最高統(tǒng)治者。自然哲學也就更成為了伊斯蘭神學的“婢女”。而在歐洲二者則出現(xiàn)了明確的分離,世俗權力歸于國王,神權歸于教皇。表現(xiàn)在哲學上,西方哲學有自然哲學和神學的較清晰分閾。阿奎那堅持上帝——自然——人三者分離的思想,認為“自然”和“上帝”是人面對的兩個實體。因此,也就相對的能更為獨立的去思考和反映人與自然包括人與“水”之間的哲學關系,并取得進展。
從中世紀結(jié)束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可歸為一個發(fā)展階段。發(fā)軔于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沖破了歐洲經(jīng)院哲學桎梏,伴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終于引發(fā)了哲學和科學的革命。康德說: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人類生產(chǎn)力水平極大的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人類開始“向大自然宣戰(zhàn)”,進而設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戰(zhàn)勝自然”被奉為圭臬,“人定勝天”成為人類的夢想和奮斗目標。水作為大自然存在的主要形式之一,這一時期對大自然的哲學認識也反映了對水的哲學認識。
培根說:我們的思想創(chuàng)造將是一種祈禱,而不是詛咒。以“人性解放”為核心的人本主義哲學帶給人類極大進步的同時,也產(chǎn)生了深刻的危機。倫敦泰晤士河污染、滇池圍湖造田即是很慘痛的教訓,黃河三門峽水庫、尼羅河阿斯旺大壩等水利工程給人們以深刻反思,至今爭議不斷。恩格斯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nèi)祟悓ψ匀唤绲膭倮瑢τ诿恳淮芜@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人類開始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
上世紀七十年代,蕾切爾·卡遜第一次把米拉米奇河等的環(huán)境保護作為一個存在于社會意識和科學討論中的概念。“爭論的關鍵主要在于卡遜堅持自然的平衡是人類生存的主要力量。把“人”的作用還原到它在物質(zhì)世界應該有的位置,而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和征服者。1972年6月12日聯(lián)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huán)境大會”,并由各國簽署了“人類環(huán)境宣言”,開始了環(huán)境保護事業(yè)。
1992年,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大會通過了里約環(huán)境與發(fā)展宣言21世紀議程,并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念,人類應與自然和諧相處,人類要改變現(xiàn)有的生活方式,要與自然建立友好的伙伴關系。同年,在愛爾蘭都柏林召開的世界水與環(huán)境會議,提出的水資源統(tǒng)一管理都柏林原則,目標是在保持生物多樣性、保證水資源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前提下提供一個環(huán)境健康、經(jīng)濟可行和社會可接受的水資源持續(xù)管理模式。
美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先后出臺了《自然與風景河流法案》《國家環(huán)境政策法》等一系列聯(lián)邦法案,表明在法律層面實現(xiàn)人與“水”哲學關系的實質(zhì)性轉(zhuǎn)變。隨后美國水壩的拆除逐漸增多,截至2015年,全美境內(nèi)拆除了超過1300座大壩,僅2012年就有65座。這些拆除項目使相應的河流和漁場獲得了重生,也折射出美國人的哲學觀,即河流作為大自然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水力發(fā)電、農(nóng)業(yè)和經(jīng)濟增長的工具。萊茵河流經(jīng)歐洲9個國家,在19世紀因為工業(yè)污染,一度被稱為“歐洲的下水道”。
經(jīng)過堅持不懈的治理,如今水質(zhì)干凈清澈,可直接飲用,成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一條河流。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經(jīng)驗就是“盡量以“自然方式”治理,恢復河流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我國在這方面起步較晚,學者李國英提出了維持河流健康生命的理論體系,標志著流域綜合管理從單純水管理向流域自然-社會-經(jīng)濟大系統(tǒng)為研究對象的流域生態(tài)學領域轉(zhuǎn)變,也可以理解為對人與“水”哲學關系的轉(zhuǎn)變。隨著我國洪澇災害、水資源短缺、水質(zhì)污染和水生態(tài)退化等問題日益突出,我們要盡快從哲學上轉(zhuǎn)變觀念,以實現(xiàn)人類活動與水環(huán)境的兼容、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
參考文獻
[1]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介[M].香港中華書局,2005.
[2]張岱年.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相關水利刊物推薦:《水資源開發(fā)與管理》(月刊)創(chuàng)刊于2003年,是由中國水利工程協(xié)會主辦公開發(fā)行的科技期刊,國際標準刊號:ISSN 2096-0131,國內(nèi)統(tǒng)一刊號CN10-1326/TV。辦刊宗旨為:關注水污染、水質(zhì)評價和水環(huán)境治理領域,傳播水資源開發(fā)利用、管理、保護和水生態(tài)治理的新成果、新技術、新經(jīng)驗,服務水利建設與管理政策研究和信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