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9-07-04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啟蒙運動自誕生之日起,就向人類昭示了其理性之內(nèi)核,理性被置于崇高的地位。然而,在努力追求理性至上和自由的過程中,康德卻提出了什么是啟蒙運動的元問題,這無異于給沉醉于理性之中的人們帶來了別樣的風景。康德通過對理性的審慎反思以及對理性的
摘要:啟蒙運動自誕生之日起,就向人類昭示了其理性之內(nèi)核,理性被置于崇高的地位。然而,在努力追求理性至上和自由的過程中,康德卻提出了“什么是啟蒙運動”的元問題,這無異于給沉醉于理性之中的人們帶來了別樣的風景。康德通過對理性的審慎反思以及對理性的批判厘清了人類理性的界限,并指出了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它不能超越經(jīng)驗和現(xiàn)象界達到對超驗世界的關照。馬克思則認為,自啟蒙運動以來,人們力求達到的理性自由只是停留于觀念上的自由,康德對于理性的批判并未觸及現(xiàn)實社會的根基,康德只是在認識論上對人類的理性進行了限制。馬克思立足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把對理性的批判轉(zhuǎn)向?qū)Y本主義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其實踐哲學實現(xiàn)了對理性批判范式的轉(zhuǎn)變。
關鍵詞:啟蒙運動;人類理性;馬克思;康德;自由;先驗;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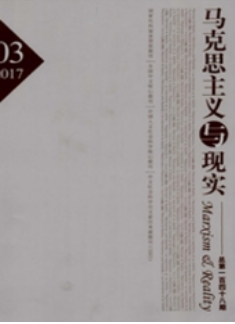
啟蒙運動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它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它代表著人類對權(quán)威的批判、對理性的渴望和對自由的追求。在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獲得了絕對的權(quán)威,在那個黑暗的時代作為彼岸世界的神學思想奴役了人類的現(xiàn)實生活,人類生活在神權(quán)的統(tǒng)治之下,人的主體性和自由受到空前的碾壓以致尊嚴盡失。那時的哲學也成了“神學的婢女”,哲學的存在是為了論證上帝存在的合理性,理性被統(tǒng)治在信仰之下。
文藝復興開啟了現(xiàn)代性的序幕,它使人的世界被發(fā)現(xiàn),人的尊嚴、價值、自由開始成為備受關注的對象。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們繼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本主義思想,肯定人的主體地位,主張對宗教神學進行批判。他們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人生本身”,如此,“對人道的愛取代了對上帝的愛,以人類通過自己的努力而達到完美的狀態(tài)取代了人類的贖罪,以希望活在未來世代的記憶之中取代了希望在另一個世界里的不朽”[1]120-121。
這是在批判宗教神學基礎上的人本思想與上帝權(quán)威的一個翻轉(zhuǎn),它不再依賴于上帝的救贖,而是立足于塵世生活,通過建構(gòu)一個充滿人性的理性主導的王國來追求人類現(xiàn)世的自由和幸福。啟蒙運動對于宗教的批判讓啟蒙高舉理性的大旗向著自由邁近,啟蒙的本質(zhì)就在于使人運用自己的理性去看待世界,使人的主體性和理性回歸于人。作為現(xiàn)代人,作為被啟蒙了的人,正如卡西爾所說:“必須而且應該拒絕所有來自上帝的幫助;他必須自己闖出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他能憑借自己的努力贏得真理,確立真理,他才會占有真理。”[2]
125自啟蒙運動以來,對啟蒙之本質(zhì)內(nèi)核———理性的探討一直都未間斷過。可以說,我們今天依然處于一個需要被啟蒙的時代。啟蒙理性自確立起,其發(fā)展就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受到過人們的崇拜,也受到過人們的質(zhì)疑和批判,但是啟蒙理性帶給人類的進步卻是毋庸置疑的。在上升和下降的跌宕起伏過程中啟蒙理性一直走在顛簸前進的路上。
啟蒙理性自身不是一個封閉的場域,它是一個向外敞開的、不斷吐故納新的開放場域,也必將在未來的無限延展中充實自身的理論內(nèi)涵。只要理性自身還存在問題,理性的啟蒙就仍然需要在場。理性的啟蒙是一個未完成的事業(yè),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理性的、批判的態(tài)度來審視理性自身,以期理性在未來的發(fā)展中能夠從不成熟狀態(tài)逐漸走向成熟,這也是理性自身的自反性要求所在。
一、康德對啟蒙理性的批判
啟蒙運動讓理性大放異彩,以致當時的人們認為任何事情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審判,只有那些符合理性的才能被保留下來。對理性的過度崇拜也造成了啟蒙理性自身的弊端,從而忽視了對理性自身的反觀和審思。當絕大多數(shù)人還沉醉在理性的勝利中時,康德卻對啟蒙自身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1784年載于《柏林月刊》第4卷的一篇文章《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中,康德開篇就對啟蒙運動做了如下定義:“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tài)。”[3]
23這是康德提出的關于啟蒙的元問題。該問題讓沉醉于理性勝利中的人們開始反思啟蒙的真正意義。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正是啟蒙理性自身所具有的批判與懷疑精神的體現(xiàn)。康德對于啟蒙的定義首先強調(diào)了人的主體性特征,人的“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不經(jīng)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3]23。不成熟狀態(tài)是自己加之于自身的,不依賴于任何他人或他物。人的不成熟并非是因為自身缺乏理性,而是因為懶惰和缺乏勇氣,把運用自身理性的能力讓渡于他人,并甘于享受這種被監(jiān)護的狀態(tài)。康德認為,啟蒙運動的口號就是“Sapere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3]
23可見,康德是將理性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希望人們能夠克服懶惰和怯懦,勇敢、獨立、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擺脫做別人意志奴隸的束縛并做自身意志的主人。康德同時還認為只要給公眾以自由,即“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3]25,那么對公眾的啟蒙就是可能的。啟蒙就是理性的運用,康德為我們區(qū)分了理性運用的兩種方式:理性的公開運用和理性的私下運用。
理性的公開運用是指一個人以學者的身份在公眾面前自由發(fā)表自己的見解;理性的私下運用是指一個人在一定的職位上所能運用的理性,理性的私下運用雖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這并不會影響啟蒙的進步。理性本身是無限的,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理性的運用卻是有限的。理性的私下運用并不影響理性的公開運用,這更加鼓勵人們要勇敢地在現(xiàn)實生活的一切事情上運用自己的理性。敢于運用自己的理智,這是一種合乎人性、充分彰顯人的自由和尊嚴的事情,這是人類所擁有的神圣權(quán)利。超脫不成熟狀態(tài)的途徑即是要做一個不受他者約束、思想自由的獨立者。
康德是一個堅定的理性主義者,他肯定了啟蒙運動對理性的彰顯,但同時他也看到了啟蒙理性自身存在的問題。以往的哲學在還沒有弄清楚理性的認識能力時就妄談知識的可靠性,這樣就難免會陷入獨斷論和懷疑論的泥淖之中。康德注意到了理性的認識能力問題,認為應該在合理的、有效的限度內(nèi)使用理性,防止因理性的濫用而導致理性淪為遏制思想自由的“他者”。對啟蒙理性的批判以及對人的自由的追求是康德哲學的兩大主題,康德正是通過在認識論上對理性的批判和重建實現(xiàn)對人自身的關照。康德對啟蒙理性的批判體現(xiàn)在他對理性效用的界分上,即“我能夠認識什么”的問題上,在對理性進行界分的過程中人的主體性和有限性被彰顯出來。
《純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對啟蒙理性進行的深刻反思,在該書中康德論證了理性在知識領域是如何行使自己的立法權(quán)的。康德一改以往哲學家所堅持的主體符合客體的觀念,反認客體要符合主體,這種對主客體符合的翻轉(zhuǎn)也即康德所實現(xiàn)的著名的“哥白尼革命”。康德吸收并綜合了經(jīng)驗論和唯理論的合理觀點,認為知識始于經(jīng)驗,但并非都來源于經(jīng)驗,對于經(jīng)驗的認識依賴于主體的先天認識能力。任何知識的形成都是人的先天認識能力,即先天直觀的純粹形式與經(jīng)驗對象的相互結(jié)合,“思維無直觀是空的,直觀無概念是盲的”[4]52。
感覺經(jīng)驗是認識的必要條件,但起決定性和支配性的卻是人的認知能力,人的先天認知能力確保了知識的必然性,由此形成的知識即“科學知識”。經(jīng)驗的形而上學便成為可能,它實現(xiàn)了主觀之于客觀的優(yōu)先性,體現(xiàn)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在自然領域知性通過為經(jīng)驗立法起到先驗性的決定作用,知性對經(jīng)驗的規(guī)定使“原本是‘綜合的’的‘經(jīng)驗’也具有‘先天性’,同時,也使原本是‘分析性-先天性’的‘邏輯形式’也具有綜合性”[5]5,這就是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
自然界是理性的認識對象,但是理性所能認識的只是現(xiàn)象,而不是物自體本身。因為知識的形成只能在時空這個可經(jīng)驗、可直觀的領域才有效,經(jīng)驗對象通過對我們感官的刺激使我們獲得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至于對表象之后的那個事物本身的認識我們是無能為力的。這就是知性的立法權(quán)限———時空,超越時空這個界限知性就無法有效行使自己的立法功能;以往形而上學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為讓有限的存在者去追求無限的物自體。“‘知性’原本是屬于‘理性’,是獨立自主的,因而是‘自由’的”[5]5,但是它要在經(jīng)驗世界建構(gòu)知識的必然王國就必然要受到經(jīng)驗世界的各種限制,可以說,理性在經(jīng)驗世界只擁有形式上的自由,在實質(zhì)上是受限制的,就如同理性的私下運用會受到公職的限制一樣。
二、馬克思對康德啟蒙理性批判的實踐轉(zhuǎn)向
康德對啟蒙理性的界限進行了厘定,他反對不加審視就盲目崇拜理性的行為,并有力地批判了視理性為萬能的觀點。這對于啟蒙理性自身的發(fā)展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康德的理性是一種純粹理性,是脫離于經(jīng)驗現(xiàn)實的抽象理性,這樣的理想主義理性觀所實現(xiàn)的自由也只能是抽象的自由。作為處于啟蒙時代的馬克思當然不滿足于此,他雖認同康德在對理性進行批判時所主張的人的有限性和主體性,但對于康德的先驗理性觀卻難以茍同。馬克思認為理性不應該是先天的、無根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現(xiàn)實根基的。馬克思立足于實踐,實現(xiàn)了對康德理性批判的實踐轉(zhuǎn)向。
三、馬克思在實踐基礎上對啟蒙理性的現(xiàn)實批判
馬克思在實現(xiàn)了對康德啟蒙理性的實踐轉(zhuǎn)向之后,又在此基礎上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啟蒙理性。啟蒙理性帶來了社會的快速發(fā)展,但是也帶來了多重隱憂。在馬克思生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啟蒙理性異化發(fā)展為資本理性,并奴役著整個人類社會。康德只是在認識論上對啟蒙理性進行批判,該批判是一種抽象的批判,不能真正觸及社會現(xiàn)實的根基。在馬克思看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zhì)力量只能用物質(zhì)力量來摧毀”[9]11。
因此,馬克思將對啟蒙理性的批判轉(zhuǎn)向了實踐———理性背后的物質(zhì)生活關系,通過對物質(zhì)基礎的批判來實現(xiàn)對社會弊端的克服,最終實現(xiàn)人類的解放。啟蒙運動確立了理性的至上性原則,使對主體性和自由的追求成為時代發(fā)展的主旋律。但是沉醉于理性勝利中的人們卻忘記了理性自身也是需要批判的。啟蒙理性本身也正是在批判宗教神學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理性自身也要經(jīng)得起審視,只有經(jīng)得起理性審視的理性才能避免走向“非理性”。
康德對于理性的批判是對理性自身的批判,是對理性合法權(quán)限的一種規(guī)定。但是康德的理性僅僅只是一種純粹理性,人的自由的實現(xiàn)只能仰望于現(xiàn)實世界的彼岸。馬克思則讓天國的自由重返人間。他認為作為有理性的人類自身的實踐活動本身就是自由的,只是由于某些外在的原因使人的自由自覺的感性活動異化,因而阻礙了人的自由的實現(xiàn),通過消滅現(xiàn)存的社會制度及其物質(zhì)基礎,在生產(chǎn)力高度發(fā)達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就能實現(xiàn)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在共產(chǎn)主義社會,人的理性與自由將得到充分的、完全的實現(xiàn),這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最終旨歸。
參考文獻:
[1]卡爾·貝克爾.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M].何兆武,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
[2]E.卡西爾.啟蒙哲學[M].顧偉銘,等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
[3]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4]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鄧曉芒,楊祖陶,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葉秀山.啟蒙與自由———葉秀山論康德[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6]俞吾金.馬克思對康德哲學革命的揚棄[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28-34.
[7]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相關刊物推薦:《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雙月刊)是中共中央編譯局主辦的密切聯(lián)系實際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綜合性理論刊物。本刊改版以來以嶄新的面貌與廣大讀者見面,注重找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當代現(xiàn)實的最佳結(jié)合點,探討有現(xiàn)實意義的理論問題和有理論意義的現(xiàn)實問題,將理論性、現(xiàn)實性、學術性、前瞻性集為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