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19所屬分類:科技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科技觀作為自然辯證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為廣大學者所青睞。哈貝馬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科技觀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探析哈貝馬斯的科技觀思想,對我國轉型時期的社會發展也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對哈貝馬斯的科技觀進行了論述,分析了
摘要:科技觀作為自然辯證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為廣大學者所青睞。哈貝馬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科技觀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探析哈貝馬斯的科技觀思想,對我國轉型時期的社會發展也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對哈貝馬斯的科技觀進行了論述,分析了其思想背景,對其思想內容進行了簡要介紹,并在此基礎上,對其思想在我國當下轉型期社會中的現實意義進行了闡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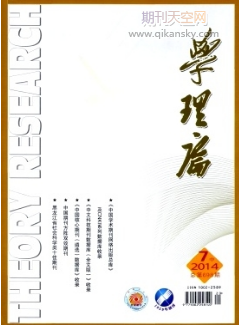
關鍵詞:科技觀;馬克思;法蘭克福學派;哈貝馬斯;現實意義
自然觀、科技觀與科技方法論共同構筑成了自然辯證法的三大核心板塊,其中科技觀尤為廣大學者所青睞。自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科學與技術日益結合成一個整體,并不斷加速發展,從多個領域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至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科技發展這一社會事實,并把其作為核心議題去研究,力求通過自身的獨特的學科視角對其進行分析探索。其中,馬克思主義科技觀及法蘭克福學派科技觀尤具代表性,法蘭克福學派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流派,承繼了馬克思關于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并經過自身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思想,對現代技術革命和現代社會進行了反思批判,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1]。在科技觀方面,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一代學者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等均從自己的學術視角出發進行了不懈探索,針對科學、技術、生產力、意識形態等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與見解,作為第二代旗手的哈貝馬斯在承繼前輩思想的基礎上,立足于社會變遷發展的實際,提出了自己的科技觀思想。
一、哈貝馬斯科技觀的思想背景
(一)學術背景
哈貝馬斯的科技觀主要是從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等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學者的思想出發進行批判性繼承與發展而形成的。霍克海默在《科學及其危機禮記》中明確指出科學作為生產力,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去促進社會文明進程。但是,當面臨作為整體的社會文明進程問題時,科學反而逃避自己應有的責任,拒絕以適當的方式處理與社會文明進程相關的問題[2];由此造成了深刻的社會危機。在此基礎上,霍克海默提出了“科學即是意識形態”的論斷。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指出并批判了技術理性主義,認為啟蒙辯證法的悲劇在于,基于技術理性出發但并沒有達到先前的理想型目標,反而被科技力量所統治,使人們處于異化狀態[2]。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指出,科學技術具有生產力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性,明確指出了科學技術本身就是意識形態,而且闡明了科學技術之所以為意識形態以及科技意識形態的消極作用,并把科學技術視為維護統治合法性的政治意識形態[2]。這些學者從不同角度論述了科技意識形態論,哈貝馬斯在承繼這些前輩思想的基礎上進行思考探索,立足于當時發展著的社會實際,形成了自己的科技觀。此外,馬克思的“科學技術即是生產力”及韋伯的“社會合理化”的理論觀點也都對哈貝馬斯的科技觀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時代背景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到來為哈貝馬斯科技觀的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哈貝馬斯認為在早期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科學與技術兩者之間雖有聯系但程度十分微弱,還沒有達到相互依賴的層次,科學也沒能對技術的發展起到加速作用,且當時傳統型社會統治的根基還很穩固,因此在這個時期科學技術既不是第一位的生產力,也不是意識形態。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到來之后,科學與技術的聯系日益緊密,在科學的助推下,技術的發展進入高速發展階段。除此之外,資本主義國家由于自由市場調節的失靈,迫切需要轉變經濟管理方式,在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影響下,國家干預經濟越來越成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態勢,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擴大政府的職能,注重政府的宏觀調控,從行政層面把握經濟的平穩運行與發展,國家的干預、調控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舊的意識形態。在此種社會情境下,科學技術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且成為意識形態的新形式。
二、哈貝馬斯科技觀內容
(一)科學技術成為第一位的生產力
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關于“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位生產力”的論斷極大程度上吸收了馬克思的科學技術與生產力間關系的觀點。馬克思是第一個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學者。哈貝馬斯在認可這一論斷的基礎上,看到當下時代科學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較之馬克思時期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在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作用已經越來越突出,已經不是簡單的有關系,而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能達到第一位生產力的層次,在這種認識下,哈貝馬斯提出了“科學技術在當今社會已成為第一位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對此論斷,哈貝馬斯從幾個不同的方面進行了論述。
第一,科學、技術及應用的一體化。哈貝馬斯認為:“技術科學化”“科學研究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依賴”“科學、技術及其運用結成一體”這些變化是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的主要依據和重要標志[3]。哈貝馬斯首先明晰了科學與技術的概念。認為科學是指關于自然、社會和思想的知識體系;而技術則是指人類征服自然所需的工具和手段,是一種能夠操作行為建筑的體系[3]。哈貝馬斯指出,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科學與技術是分離的,即便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珍妮紡紗機、蒸汽機等新興產品的出現也只是為了解決現實生活中遇到的難題,提高生產效率,并不是科學研究的產物,此時技術優先于科學。直到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后,電力開始廣泛地應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科學研究才與技術應用更緊密地開始聯系到一起,科學研究開始指導技術應用的發展,在二戰后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科學研究與技術發展之間的作用力空前加強,技術在科學研究的催化作用下加速發展,至此,科學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程度進一步加深,并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哈貝馬斯指出,“在進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技術的科學化趨勢不斷加強,技術與科學的鏈接催生了大規模的工業研究,工業研究則直接被應用于實用領域,自此,在不斷地研發、回饋、應用、磨合的過程中,科學、技術與應用不斷結合成一個體系,且其一體化程度不斷加強,隨著社會的發展,最初被應用于科研、軍事等領域的產品開始逐步流向市場,向人民生活靠近。隨著民用商品生產部門的科學與技術的普及,科學與技術便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4]科學、技術與應用的一體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學技術向生產力轉化途徑的變化,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基于生產主位的技術發展與科學研究,而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科學研究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漸漸演變為科學主位出發從而轉化為技術進而轉化為生產。并進而形成一種“科學—技術—生產—技術—科學”的循環,在相互循環中,科學成為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最為關鍵的動力因素,實現了從之前的間接發揮作用到現在對生產力直接影響的身份轉變[5]。此外,隨著科學、技術與生產力三者之間一體化程度的加強,科學技術向生產力轉化的物化周期也大大縮短,由之前的間接轉化到現在的直接轉化,其作用力日益凸顯,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做出了“當下時期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生產力”的論斷。
第二,國家干預的加強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互為因果、相互促進。鑒于此前市場調節的失靈,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歐美國家大都基于凱恩斯主義視角,采用國家調控經濟的手段,以期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來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這樣,經濟職能的發揮便由此前的市場轉移到了國家手中,國家機器要采取措施保證經濟的平穩發展,必須要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家干預的制度化為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提供了重要的中介條件。一方面,國家通過對科學與技術方面資金、人才等的投入,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基于其第一位生產力的優勢,反作用于經濟,促進社會的良性運行及經濟的快速有序發展。科學技術與國家干預之間的相互作用,互為因果,從而有效地促使科學、技術與生產力三者之間的一體化,科學技術成為直接形態的第一生產力[3]。
第三,科學技術已成為經濟增長的獨立變數。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個突出特征便是信息化、知識化,無論什么產業、工業,其發展更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先前單單依靠體力勞動產生經濟價值不同,當下的科學技術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由腦力勞動所創造的科學技術已經成為剩余價值的獨立來源。其次,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處事方式、道德觀念等都因受到科學技術的影響而發生了重大變化,科學技術“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成了理解一切問題的關鍵”,科學技術因此也就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的“獨立系統變數”[6]。
(二)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
將科學與技術作為意識形態,哈貝馬斯并不是第一位發現其關聯性的學者。《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是哈貝馬斯在紀念馬爾庫塞誕辰70周年時所作,是對馬爾庫塞觀點的承繼、回應與思考。馬爾庫塞在承繼霍克海默思想的基礎上做出了科學技術即是意識形態的論斷。哈貝馬斯批判性地繼承了馬爾庫塞的觀點,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的時候才具有意識形態的特點[7]。哈貝馬斯首先明確區分了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所呈現出來的不同的意識形態,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是基于神學、宗教的政治統治,其意識形態特點是“自上而下”所建立的;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科技成為第一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在此時,社會的意識形態所呈現出來的特點是基于科技所影響的人類生活的自身實際的“自下而上”所建立的[8]。社會不同時期的意識形態是不同的,故而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地說“科學技術是意識形態”,應對其做出范圍的限定。故而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時,其才具有意識形態的特征。
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科學與技術間的聯系是松散的,但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與應用的一體化使得科學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科學與技術在這一時期已成為第一位的生產力。國家干預經濟使得原有意識形態瓦解,國家干預與科技發展之間互為因果,相互加強,在此種意識形態空缺的情況下,政治統治需要有一種新的合法性的根基,原有的“統治的”合法性已不合時宜,技術的科學化、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優勢不斷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不斷影響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與道德觀念等,科學技術逐步成為國家進步的關鍵性力量,隱隱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無形中擁有了合法性基礎[9]。在此種情況下,科學技術成了意識形態的新形式。
其次,由于科學技術在成為第一位生產力之后,已變成了剩余價值的獨立要素。在此種情況下,人們更加注重的是技術本身所帶來的物質財富,至于政治問題、制度問題,人們對其關心程度逐漸下降,技術在不斷地滲透中引發了一種韋伯所說的目的合理性行動,人們更加注重的是最終所要達到的結果,只要結果是滿意的,那么這種制度便能夠受到民眾的支持,至于制度本身并不是人們所關心的。故而,目的合理性更大程度上引發的是人們對技術問題的關心。梳理哈貝馬斯的思路可以發現:由于國家干預經濟來彌補市場調節的失靈,國家機器承擔了經濟職能,經濟問題轉變為政治問題,與此同時,由于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位生產力的優勢,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基礎轉變為科學技術,政治問題轉變為技術問題,技術問題更多地解決了人們生活中所面臨的方方面面的難題,人們更加關心技術,更加注重的是目的合理性,而非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交往合理性,在隱隱中技術便有了深厚的根基,從而為統治合法性提供了基礎[7]。
三、哈貝馬斯科技觀的現實意義
哈貝馬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學者中的代表性人物,其科技觀一定程度上承繼了前輩們的思想觀點,在自身思考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視野,對于其科技觀,許多學者已經進行了自己的分析論證,其觀點有合理之處,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萬事萬物都有兩面性,這是無可置疑的,但不妨礙我們從他的思想中吸取精華,借鑒經驗,為我國當下的發展助力。故而認識和學習哈貝馬斯的科技觀,對我國當下轉型期社會的平穩有序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經濟場域來看,該場域的核心問題是經濟與利益。改革開放以來,科學與技術開始進入公眾視野,更大程度上地應用于經濟發展。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重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馬克思主義論點。在國家政策和戰略的指引下,科學技術被更好地開發與利用,更好地發揮其生產力轉化的優勢,極大程度上助推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我們也應注意到,科學技術在向生產力轉化的過程中,因地區之間先天條件的差異,其生產力轉化的程度會產生差別,久而久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會產生質的差異,尤其是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距,這是我們在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不能回避且不得不去面對的問題。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通過科技致富、產業致富,更好地幫助人民提高生活質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高度的責任感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工作。更大程度上激發貧困地區的優勢與潛能,從而更好地發揮科學與技術的生產力優勢,助力農民脫貧致富。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我們需要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位生產力的優勢,助推脫貧攻堅,促進經濟的平穩有序發展。
從政治場域來看,該場域的核心問題主要表現在權力層面。在哈貝馬斯看來,科學與技術是一種新形式的意識形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統治形式。權力所反映出來的問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利用科學技術這種途徑來窺探一二,哈貝馬斯認為,科學技術的合法性基礎,隱隱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那么,基于目的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之間的相互協調,通過科學技術來發揮其意識形態的功效,有利于政治生態的風清氣正。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不斷深入,立足科技理性,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除此之外,政治場域也更加注重人的主體參與,國家充分尊重人民的主體性地位,“基層自治制度”、社會治理法治化、德治相結合等均體現了“人文理性”的關懷。
從文化場域來看,該場域的核心問題主要表現在價值觀層面。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伴隨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迅速變遷而來的是固有價值觀念與當下價值觀念之間的錯位,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的價值觀沖突,也引發了相應的道德滑坡事件。與齊美爾的文化悲劇論述相似,哈貝馬斯也提出,科學、技術及其應用的一體化極大程度上加深了科技的地位,從而加深了人們對科技的崇拜,科技仿佛無所不能,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可以通過科技來解決,人們越來越關注于科技本身,科技統治的步伐似乎就在不遠處,所造成的一個結果是人們越來越關注于目的合理性而非交往合理性,目的合理性所指涉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交往合理性所指涉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此造成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失調。意識形態與價值觀之間存在很大關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在價值觀的形成、發展、傳播過程中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故而,應從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的功效出發,傳播正確的價值觀,幫助公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并付諸實踐去踐行、落實,從而改善文化場域的環境,促進交往合理性。
從社會場域來看,該場域的核心問題更多地表現在民生層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階層分化凸顯。陸學藝認為當前我國社會可以分為十個階層,各個階層擁有不同的社會資源。階層結構形態類似于一種準洋蔥型的結構形態,中產階級不斷變大,底部不斷變小。隨著階層結構變遷,社會資源、社會地位改變產生的心理不平衡感誘發了社會沖突。社會作為一個特定場域,其階層問題所引發的民生問題有其自身的社會情境,景天魁曾形象性地提出“時空壓縮”這個概念來概括改革開放的中國所面對的獨特的時空特征,即傳統性、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前所未有的交匯、沖撞、整合。傳統的、現代的、后現代的思想、方式等統統壓縮在這個時空場域里面。面對此種“時空壓縮”,我們該怎樣實現“超越進化”,實現傳統性、現代性、后現代性的有機統一,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以求達到人和社會更好的發展,從哈貝馬斯的科技觀中我們可以窺探出一些啟示。
相關期刊推薦:《學理論》雜志創辦于1959年,是社科綜合類學術期刊,本刊具有學術性、探索性和時代性的特點,刊載具有理論價值和實際應用價值的學術精品,充分反映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是我國具有悠久歷史的重要學術載體。設有:科學發展觀、新農村建設、政治理論、思想研究、社會學、民族學、檔案?圖書管理學和法學、哲學、經濟學、教育學、文學、史學等欄目
從生態場域來看,該場域的核心問題更多地表現在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層面。從人與自然關系層面來看,從“四位一體”到“五位一體”,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現代化建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哈貝馬斯指出,隨著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注重于目的合理性而忽視了交往合理性,造成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失調,在發展過程中,人類也逐漸意識到生態關系的重要性,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習近平同志指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要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像保護生命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將生態建設列入政績考核,不斷完善相關體系制度,在經濟發展中更加注重生態效益。近幾年,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人文理性不再被處于遺忘的角落,越來越得到注重。在發展中更加注重人的地位與作用,不再僅僅是單方面注重科技理性,更加注重科技理性與人文理性的協調發展。在當代社會,道德意識不斷覺醒,不管是學者還是普通公民,大家越來越關注于人自身,更加注重倫理規范以及科技理性與人文理性之間的度的把握,促進科技理性與人文理性的有機協調。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在經濟場域、政治場域、文化場域、社會場域、生態場域都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績,如精準扶貧、反腐敗斗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民生保障、生態建設等,但與此同時,各場域還有相當一部分問題需要更好地解決或完善。不可否認,哈貝馬斯的觀點也有其狹隘與不合理之處,故而我們應合理吸收其精華,大力發展其思想的精髓,發揮科技作為生產力的優勢條件,堅持科學發展觀,協調科技理性與人文理性,從而指導我國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有機協調發展。
(一)大力發展科技,發揮其生產力優勢,助推經濟發展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事實證明,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是一條正確的路徑選擇,我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績。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綜合國力的競爭,而綜合國力的表現便是科技實力,科技實力與經濟實力的發展需要科學技術的發展引領,為此,我們應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充分發揮其對社會發展的引領與助推作用。與此同時,我們要注意科學技術與生產力轉化之間的關系,加快實現科學、技術、生產的一體化,從而縮短物化周期、加快生產進程,更快地將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
(二)堅持科學發展觀,促進科技理性與人文理性的協調發展
哈貝馬斯在《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中論述了科學技術通過影響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道德觀念等而造成的片面迷信工具理性,進而造成人與自然關系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失調狀態。哈貝馬斯指出,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了人們過于注重工具理性行為而忽視了交往理性行為,這些觀點是我們在社會發展中應予以借鑒的。我們在發展科學技術,通過科學技術發展社會經濟的同時,也應注意科技理性與人文理性之間的協調,不能任由科技理性一家獨大,最終造成人文理性的泯滅與消失,形成一種失控的技術統治狀態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科技理性與人文理性可以說是一體兩面,離開了科技理性單純發展人文理性,少了科技的指引,會使社會陷入停滯的發展狀態;離開了人文理性單純發展科技理性,會使科技理性發展到極致,從而出現科技統治人類的文化悲劇。進入21世紀,黨中央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更加關注人自身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更加強調科技理性與人文理性的協調。在此基礎上,發揮科學技術的生產力作用,從而更高效地去促進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哈貝馬斯離開社會情境談論技術理性的不合理之處,哈貝馬斯在談論技術理性之時并沒有立足于當時的生產方式、政治制度等特定社會情境,從而認為技術本身具有統治性的技術悲觀主義,忽略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技術原罪論”,我們應看到哈貝馬斯在這一方面的不合理之處,在發展科學技術的過程中,我們應如“知識社會學”所提倡的那樣,注重知識的“社會情境性”,將知識根植于特定的文化類型中,立足于我國國情及社會實際,合理利用科學技術,促進社會的平穩有序運行和人的全面發展。——論文作者:王帥博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