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04-24所屬分類:醫學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探討中醫術語肝的起源與演變,可以發現肝的能指/所指關系發生過多次轉移:物質實體功能概念物質實體。肝的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揭示了肝的意義指向,以及在整個符號系統中的地位。肝的隱喻和轉喻同樣揭示的是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隱喻的基礎是相似,轉喻
摘要:探討中醫術語“肝”的起源與演變,可以發現“肝”的“能指/所指”關系發生過多次轉移:物質實體→功能概念→物質實體。“肝”的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揭示了“肝”的意義指向,以及在整個符號系統中的地位。“肝”的隱喻和轉喻同樣揭示的是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隱喻的基礎是相似,轉喻的基礎是相近,以此可以說明中醫“肝”概念的形成過程。從歷時上考察,“肝”的所指存在混亂和邊界不清的情況。在目前中醫藥術語規范體系中,尚缺乏一個重要術語“肝系”。“肝系”一詞的使用,具有詞頻和理據兩方面的合理性,且具有較強的區分度和解釋功能。“心系”“脾系”“肺系”“腎系”等同級別名詞也應相應增加,才符合系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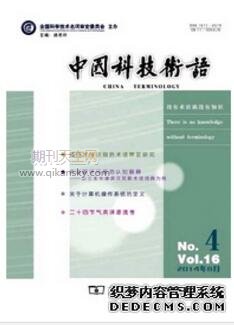
關鍵詞:肝;肝系;符號;藏象;隱喻;中醫語言;術語規范
一中醫術語“肝”的起源與演變
1.從物質實體到功能概念符號
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索緒爾(Saussure)用所指和能指分別代替概念和音響形象,并說“能指和所指的聯系是任意的”,而且同時具有“不變性和可變性”,常常發生“能指和所指關系的轉移”[1]102-112。
相關期刊推薦:《中國科技術語》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術語學理論、促進全球華語圈科技術語的規范和統一。要介紹國內外術語理論研究成果,公布規范科技名詞,發布試用科技新詞,組織重點、難點科技名詞的定名討論,探究科技術語的歷史文化內涵,報道科技名詞規范工作動態,是促進術語學在我國發展的權威雜志,是及時發布規范漢語科技名詞的媒體,是集中展現我國科技名詞術語審定工作情況的窗口。
“肝”曾明確地指物質實體,即人或動物的內臟中的肝臟。《莊子·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這是肝這一臟器作為物質實體被人類認知,并形成語言符號的例證。“肝”的文字形體,“從肉,干聲”(《說文解字》),也說明“肝”首先是作為物質實體的符號存在的。在《黃帝內經》中,“肝”指物質實體也是明確的,《素問·刺禁論》說“肝生于左,肺藏于右”,《靈樞·經脈》說肝足厥陰脈“挾胃屬肝絡膽”,“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靈樞·天年》說“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難經·四十一難》說“肝獨有兩葉”,《四十二難》又說“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這些論述不管正確與否,至少表明人們知道人體中有肝臟這一臟器,且對人體肝臟進行過觀察。盡管此后中國的解剖科學未能很好地發展下去,這種“能指/所指”關系的符號“肝”在后世仍被繼續使用,直至今天。
幾乎就在“肝”指物質實體的同時,“肝”被描述具有某些特定的人體功能。《內經》中,關于“肝”的功能的描述可謂比比皆是,如《素問·六節藏象論》:“肝者,罷(疲)極之本,魂之居也。”《素問·靈蘭秘典論》:“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素問·經脈別論》:“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于筋。”《素問·痿論》:“肝主身之筋膜。”《素問·平人氣象論》:“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氣也。”《素問·五藏生成》:“人臥血歸于肝,肝受血而能視。”《靈樞·本神》:“肝藏血,血舍魂。”《靈樞·脈度》:“肝氣通于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這些功能描述,表明“肝”的所指已經豐富了許多,而能指卻沒有變,實際上就已經發生了“能指/所指”關系的轉移。今天我們來審視這種轉移,其實帶來了不良的混亂后果。現代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證實,作為物質實體的人體肝臟的功能,很難和中醫描述的“罷極之本”“魂之居”“謀慮出”“散精”“主身之筋膜”“藏血”等功能完全等同起來。這些功能應當和肝臟的部分功能以及更多的人體器官組織功能有關,如腦及神經系統。功能與實體脫離,這種現象可以解釋為古代解剖學不夠進步,也可以解釋為當時人們對物質實體肝臟的功能了解不夠。但不管怎么說,這是已經發生的語言事實。索緒爾說:“語言根本無力抵抗那些隨時促使所指和能指的關系發生轉移的因素。這就是符號任意性的后果之一。”[1]113
2.“肝”的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
符號的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最能體現符號與符號之間的區別與聯系,以及說明符號在語言系統中的地位。綜合《內經》各篇所述,我們可以發現經常與“肝”發生組合關系的有五方的“東”、五時的“春”、五氣的“風”、五化的“生”、五行的“木”、陰陽的“少陽”、五腑的“膽”、五體的“筋”、五官的“目”、五華的“爪”、五色的“青”、五聲的“呼”、五味的“酸”、五志的“怒”。且“肝”與“心”“脾”“肺”“腎”形成五臟的聚合關系,與“膽”形成臟腑表里的聚合關系,與“心”形成相生與受資(母與子)的聚合關系,與“脾”形成相克與受制的聚合關系。如此等等,最終就形成中醫學的“四時五臟陰陽”系統結構。
但是,即使是依靠這種看起來比較嚴格的區別與聯系建立起來的“能指/所指”關系,仍然會存在混亂或邊界模糊不清的情況,而且在時間的軸上或不同語言環境中仍然會發生關系的轉移。比如章太炎就指出:今文《尚書》肝配木、心配火、脾配土、肺配金、腎配水,古文《尚書》則脾配木、肺配火、心配土、肝配金、腎配水,《禮記·月令》與古文《尚書》匹配方法相同,鄭玄注經時則前后矛盾[2]。
此外,《內經》中原本僅有“肝生筋”“肝主身之筋膜”“肝藏筋膜之氣”,即“肝主筋膜”之說,但后世朱丹溪又倡導“肝主疏泄”之說。《格致余論·陽有余陰不足論》:“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按《內經》理論,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包絡者,心主之脈”(《靈樞·邪客》),十二經脈弛張運動,均由心包之筋主宰,經脈弛張異常必然影響氣血津精液疏泄異常,為什么又說“肝主疏泄”呢?當代方劑學家陳潮祖解釋說,《內經》之前,古人將臟腑分為六臟六腑,在《內經》中開始將六臟中的腦外包膜分屬心、肝二臟,成為五臟六腑,但論述經絡時卻仍以十二經絡并存。“古人將其六臟六腑,十二經脈,分為手足三陰三陽,為了論述簡便,只言其足而不言手,其實手經亦在其中,只因代遠年湮,現已淡忘。”[3]其實在《內經》中“肝”就至少具有兩種意義指向,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以肝、心、脾、肺、腎為五臟,而《素問·靈蘭秘典論》中以心、肺、肝、膻中(心包)、脾、腎、膽、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為十二臟,“肝”在其中的功能意義就變得不盡相同。后世的“肝”的意義指向則或此或彼,變得混沌不清。
3.“肝”的隱喻和轉喻
符號與符號之間,還有一類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是由隱喻和轉喻產生的。隱喻以相似性或類比為基礎,轉喻則以接近的或相繼的聯想為基礎。
“肝”在古代文獻中以“木”為喻最為常見。《素問·金匱真言論》“其類草木”馬蒔注:“肝性柔而能曲直,故其類為草木。”《難經·四十一難》:“肝者東方木也,木者春也,萬物始生,其尚幼小,意無所親,去太陰尚近,離太陽不遠,猶有兩心,故有兩葉,亦應木葉也。”因“肝”似“木”,因此后世又有“性喜條達”“惡抑郁”之說,《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木郁達之”,滑壽注“木性本條達”,即意象樹木枝葉喜自由伸展,不受抑制。在這個隱喻中,“肝”與“木”形成的是一種聚合關系。《素問·靈蘭秘典論》:“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肝”與“將軍”形成隱喻,它們之間的關系也是聚合關系。雖然隱喻具有相似性,但我們應該認識到這種所謂的相似不是絕對的,只是以類比的方法來解決符號的所指不易描述的問題。
“肝為血海”也是一個隱喻,但它的出現時間比較晚,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大約在宋元之際。《素問》僅見“人臥血歸于肝”,王冰注“肝主血海”,《素問·上古天真論》“(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王冰注“沖為血海,任主胞胎”,且《靈樞·海論》“沖脈者,十二經之海”,張介賓注:“此即血海也”,皆未言“肝為血海”。宋代嚴用和《濟生方·婦人門·崩漏論治》稱“肝為血之府”。明代李梴《醫學入門·臟腑·臟腑條分》:“人身動則血行于諸經,靜則血藏于肝臟,故肝為血海,心乃內運行之,是心主血也。”始言“肝為血海”,明代李中梓《內經知要·藏象》亦謂之。此后此說漸盛,故后世認為血海有二,一為沖脈,二為肝。清代陳修園《金匱方歌括·赤小豆當歸散》:“肝為血海,氣通胞中,主宣布之權,虛則失其權矣。”唐容川《血證論·吐血》:“血海胞中,又血所傳輸歸宿之所,肝則司主血海,沖、任、帶三脈,又肝所屬。”已將沖、任、帶三脈皆劃歸肝所屬系統。如同“女子以肝為先天”一樣,“肝為血海”也遭到了不少醫學理論家的質疑[4],但作為一種由隱喻形成的符號聚合關系,就更難評判其正誤了,因為這樣言說的基礎,不過是因為它們相似。
轉喻的特點,是用具有組合關系的符號進行替換,古代醫學典籍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如李中梓《醫宗必讀·乙癸同源論》:“東方之木,無虛不可補,補腎即所以補肝;北方之水,無實不可瀉,瀉肝即所以瀉腎。”其中的“東方之木”就是“肝”的轉喻,因為“肝”是“東方之木”的對應之臟。轉喻和隱喻之間并沒有嚴格的區分界限,有時候轉喻也因為相似性而形成,隱喻也由鄰近性而形成,因此在古代醫學典籍中“木”仍然是“肝”最常見的轉喻。與“肝”相關的符號可以替代“肝”,但其前提條件是這種符號關系為人熟知,接近的或相繼的聯想可以自然產生。《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故實脾,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對于這段記述,后世醫家將其描述為“培土榮木”“清金益木”“滋水涵木”,也是因為“肝”與“木”的關系為人熟知。此外又有“子令母實”一說,“母”是“肝”的轉喻,因為“肝”生“心”的關系也是為人熟知的。有些符號之間的關系并不那么為人熟知或并不固定,采用轉喻就會帶來理解上的困難。如《難經·七十五難》:“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這段記述中“子”“母”究竟轉喻哪一臟,歷來爭議很大,就是因為“子”“母”與“肝”“心”“脾”“肺”“腎”的符號關系并不固定。
隱喻和轉喻不但能解釋古代醫學文獻中“肝”與其他符號的關系,而且我們還能用它來說明“肝”符號的“能指/所指”關系是怎樣發生轉移的。隱喻的相似性有兩種: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在“肝”與“將軍”的隱喻中,源域“將軍”與目標域“肝”,就是一種僅存在于人的主觀上的心理相似性。人腦通過概念性映射,將一種新的意義強施于目標域。隱喻的基礎既是相似性,就表明它不是絕對客觀的,而是相對于人們的經驗而言的,是可以創造的。但正是由于認知符號學解釋項的參與,才使得中醫學理論的發生和發展具有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和發展永續的活力[5]。它表現在語言序列中,就是“肝”的詞義已經發生擴展和變異。而且轉喻和隱喻在詞義的延伸中有時會交叉或相互作用。轉喻的基礎是鄰近性,這意味著它不僅存在于部分與部分之間,還可以存在于部分和整體之間,即用部分代替整體,如用“肝”代替“肝”和“心包”這個整體,或代替“肝”和“沖、任、帶三脈”這一整體。以此,就可以解釋為什么“肝”的所指意義越來越寬,范圍越來越廣。
4.西醫傳入對“肝”的影響
李經緯說:“西洋醫學傳入我國,其歷史也很悠久。但若就其有連續性、有現代醫學概念,并伴隨著文化傳入性質而來者,則大約始自16世紀。”[6]在16世紀的英語語言符號系統里,liver這個單詞明確指物質實體的肝。在解剖學上,它界限明確,僅包括肝體部分。在肝的功能的認識上,也幾乎達到了現代醫學的認識程度。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論》,是根據直接的觀察來寫作的人體解剖學教科書,其中對肝臟的認識已經達到比較深入的程度。而中國的王清任在1830年始著成《醫林改錯》一書,才比較正確地論述了肝與胃、胰、膽的復雜關系。由此可見,liver一詞雖然較為接近漢語表示物質實體的“肝”,但仍有較大的不同,而與表示功能意義的“肝”相比,重合的部分已經很少。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就指出:“中醫藥學的大部分用語在歐洲語言中都缺乏對應語”[7]。
當時漢語怎樣表達liver一詞的含義,面臨著一個復雜的局面。按照語言接觸的一般規律,漢語原本也可有多種選擇,比如直接向英語借詞,或者利用漢語自身的材料和規則構成新詞。但漢語最終的選擇是沿用舊詞“肝”,從而使“肝”的“能指/所指”關系再一次發生了變異。“肝”的變異只是一個側面,實際上在19世紀之后,當中醫學與西醫學開始發生激烈的碰撞,漢語的醫學語言符號系統也變得異常復雜起來。1847年,戴維編撰的《初學者入門》,采用中英文對照的形式,介紹西醫的解剖、疾病、藥物等用語,“肝”完全等同于英語liver一詞的意義。大約與此同時,前述陳修園、唐容川等正在其著作中論述“肝為血海”的理論。
今天,來自西醫的語言符號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對“肝”的釋義:“人和高等動物的消化器官之一。人的肝在腹腔內右上部分,分為兩葉。主要功能是分泌膽汁,儲藏糖原,調節蛋白質、脂肪和糖類的新陳代謝等,還有解毒和凝血作用。也叫肝臟。”這表明進入現代漢語基本詞匯的“肝”,實際上來自西醫語言符號系統而不是中醫。
二中醫術語“肝”的規范及存在的問題
1.“肝”及相關術語的規范
朱建平認為,中醫藥學的術語體系在《黃帝內經》時代就已經初步形成[8]。西醫術語進入漢語語言系統雖然較晚,卻發展迅猛。在西醫術語加入之后,現代醫學術語中就形成了兩套術語系統共存的狀況,“肝”的情況只是一個縮影。面對“肝”這一術語的復雜情況,術語工作者采取按不同學科的不同名詞來加以規范。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公布的《人體解剖學名詞》“肝”位于“內臟解剖→內臟學,消化系統”下,《組織學名詞胚胎學名詞》“肝”位于“消化腺”下,英文等價術語都是liver。而同樣是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公布的《中醫藥學名詞》,“肝”位于“中醫基礎理論→臟象”之下,定義為:“五臟之一,位于腹部,膈之下,右脅之內。其主要生理功能是主疏泄和主藏血,并與筋、目密切相關。”英文等價術語還是liver。
中醫藥術語規范也引進了部分西醫術語,如“肝硬化”“肝癌”,但又采取了“病+證”的方式加以細化,如“肝癌·肝陰虛證”“肝癌·氣滯血瘀證”“肝癌·濕熱蘊毒證”“肝癌·脾虛濕困證”“肝癌·肝腎陰虛證”“肝癌·肝氣郁結證”。英文等價術語,“肝癌·肝陰虛證”為livercancerwithsyndromeofliveryindeficiency,“肝癌·肝氣郁結證”為livercancerwithsyndromeofliverqidepression。
術語規范設置“足厥陰肝經”條,位于“中醫基礎理論→經絡”之下,英文等價術語為JueyinLiverChannelofFoot或JueyinLiverMeridianofFoot。
此外,當前的中醫術語規范,還將一系列歷史上形成的固定陳述收進來,形成短語類型的術語,如“肝主升發”“肝主疏泄”“肝為剛臟”“肝體陰用陽”“肝主筋”“肝藏血”“肝藏魂”“肝開竅于目”“肝惡風”等。英文等價術語,“肝主疏泄”為livercontrollingconveyanceanddispersion,“肝主筋”為livergoverningtendons。
“肝為血海”“肝主藏血”在《中醫藥學名詞》中沒有立條,但設置了“血海”條,定義為:“(1)婦女沖脈。(2)婦女肝臟。二者均在調節婦女月經方面起重要作用。”英文等價術語:bloodsea。
2.“肝”及相關術語存在的問題
當前對“肝”這一術語的規定,雖然限定了不同的學科,仍然缺乏明晰的區分度。在中醫診治實踐或科學研究的大多數語境中,需要同時提及肝實體和傳統“肝”概念,仍然一律用“肝”這一術語,使得各種表述含混而冗雜。又如“肝癌·肝陰虛證”“肝癌·肝氣郁結證”等術語,若不明其中各個“肝”的區別與聯系,則診治無從著手。關于“肝”的英譯也是如此。
有人認為,按照慣例,“肝”在行文中如果不是特別強調,都是指西醫的肝臟,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實際上這種情況已經極大地造成了術語系統的混亂。術語規范工作的意義在于積極改變容易造成混亂的部分,而不是一味遵從“約定俗成”。
從解釋功能上看,作為中醫藥學名詞的“肝”仍然是含混不清的:中醫學的“肝”很難說就是位于腹部膈下那個五臟之一,英文liver與中醫的“肝”更非完全一致。這種籠統的定義限制了“肝”的解釋作用。“足厥陰肝經”是專有名詞,僅適用于對經絡的解釋。“肝主疏泄”“肝主筋”“肝藏血”等短語性術語及隱喻性術語“血海”,對“肝”解釋功能不足的缺陷有所補充,其優點是具有歷史文獻來源,缺點是過于煩瑣且不易理解。
三“肝系”一詞作為規范術語的建議
1.“肝系”的詞頻和理據
目前有的中醫學著作、論文為了將中醫“肝”概念與西醫肝臟相區別,就將其另行命名為“肝系”。如陳潮祖在《中醫治法與方劑》中就使用了“肝系”一詞。又以中國知網(CNKI)檢索為例,截至2019年7月19日,以“肝系”為主題詞共有163篇中文文獻,以“肝系”為關鍵詞共有58篇中文文獻,這說明“肝系”一詞已經有了一定的使用率和認可度。
綜合各種文獻所述,“肝系”是按中醫五臟功能劃分的概念,以區分物質實體的人體肝臟概念。從理據上來說,這個概念實際上在《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素問·金匱真言論》等篇章中就已出現,雖然以“肝”稱之,但肝、膽、筋、目均在其內,它不但包括“足厥陰肝經”,還包括“手厥陰心包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甚至“沖、任、帶三脈”循行部位的功能。這些部位相互關聯,形成系統,功能上共同起作用或相互牽制,所謂“肝主筋膜”“肝主疏泄”“其類草木”“肝主血海”“肝主藏血”“性喜條達”“惡抑郁”的描述皆出于此。古代漢語重意不重形,很多時候本來該表達成“肝系”的地方,都用“肝”表達了。中醫的“肝”概念,其實就是在古漢語以木喻肝并以實體代功能、局部代整體的語言環境下產生的。這個概念在現代中醫藥學中仍然廣泛使用,但與物質實體的人體肝臟已經無法完全對應,實際上對應得更多的是肝、腦、心及神經系統、循環系統的某些器官組織的功能。從唯物的觀點來看,中醫“肝”的各種功能不應當沒有物質基礎,而這個物質基礎應當表述為“肝系”。從“肝”歷史發展過程來看,“肝”的演變經歷了比較復雜的過程,也應當對原術語“肝”的不同義項進行分化,但又不宜過于煩瑣。因此在目前中醫藥術語的體系中,出現一個名為“肝系”的重要術語,也是必然的。
語言規范有兩個基本原則,一是詞頻,二是理據。“肝系”一詞的出現完全符合這兩個原則,因此筆者認為這一命名是可取的。英文等價術語可采用“音譯+意譯”的方式:gansystem。這樣既可以和liver區別開來,又可以體現中醫術語的民族性。
2.“肝系”的區分度和解釋功能
“肝系”一詞具有較強的區分度和解釋功能,可以略舉幾例以說明其實用意義。比如病、證方面,西醫學中的“肝炎”“肝硬化”“肝癌”中的“肝”,與中醫學的“肝腎陰虛”“肝陽上亢”“肝風內動”“肝氣郁結”“肝火上炎”“肝陰虛”“肝血虛”中的“肝”大不相同,因為它們屬于不同的符號體系,西醫學名詞與中醫學名詞之間無法畫等號。但不能畫等號,并不意味著二者之間沒有聯系。事實上,不同體系的名詞大致相當的情況仍然是存在的。比如張錫純就認為中醫的“內中風”“煎厥”“大厥”“薄厥”相當于西醫的“腦充血”(規范術語為“腦卒中”)。《醫學衷中參西錄》“鎮肝熄風湯”條說:“風名內中,言風自內生,非風自外來也。《內經》謂‘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蓋肝為木臟,木火熾盛,亦自有風。此因肝木失和風自肝起。”“西醫名為腦充血證,誠由剖解實驗而得也”“而《內經》初不名為內中風,亦不名為腦充血,而實名之煎厥、大厥、薄厥。”上述情況,雖言“鎮肝”,實際上病變部位不僅在肝,更涉及屬“肝系”的腦。如“肝”與“肝系”兩個術語并行使用,則能區分相關的概念,又顯示出相互之間的聯系。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