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12-03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孫奇逢是明末清初的北方大儒,耿介為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學家,是孫奇逢晚年所收重要弟子之一。孫奇逢與耿介亦師亦友,情誼深厚而師友之道傳。通過詳細梳理二人交游的具體情況,可以明晰耿介晚年向學的具體情況和他在弘揚和發展夏峰學術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摘要:孫奇逢是明末清初的北方大儒,耿介為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學家,是孫奇逢晚年所收重要弟子之一。孫奇逢與耿介亦師亦友,情誼深厚而師友之道傳。通過詳細梳理二人交游的具體情況,可以明晰耿介晚年向學的具體情況和他在弘揚和發展夏峰學術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時也能了解二人在志節、思想等方面的頗多細節,意義重大。
關鍵詞:孫奇逢;耿介;交游;夏峰學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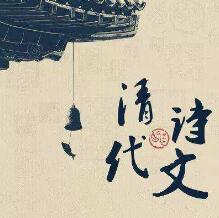
孫奇逢是明末清初與黃宗羲、李颙并稱的三大儒之一,身處天崩地解的明清嬗遞時代,堅守遺民立場,其學術“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不拘泥于門戶之見而氣魄獨大,提倡學以致用、躬行實踐,對當時的士大夫,特別是北方學者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耿介(1623―1693),初名沖壁,因讀《北山移文》見“耿介拔俗”句而更名,字介石,號逸庵,世稱嵩陽先生,登封人。耿介學宗程朱,又特別看重周敦頤,中年以前宦海沉浮,辭官后經湯斌介紹拜入孫奇逢門下,專研理學,著述頗豐,同時主持嵩陽書院,培養出姚爾申、孫祚隆、梁家惠等中州名儒。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載:“陳文恭撫豫時,嘗以先生(李來章)及夏峰(孫奇逢)、潛庵(湯斌)、逸庵(耿介)、靜庵(寇克勤)、起庵(張沐),合以張敬庵(張伯行)、冉蟫庵(冉覲祖),為中州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并祀鄉賢。”[1]耿介與老師孫奇逢同列中州八先生之席,可見他實乃孫奇逢晚年所收重要弟子,而耿介和孫奇逢交游的具體情況以及他對夏峰學派的發展和傳承之功卻少有學者論及。因此,本文對孫奇逢、耿介二人交游情況加以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一、孫奇逢與耿介交游的淵源
清康熙六年(1667),耿介為母服三年喪后起復入都,仕途再遭打擊,遂絕意仕進,自稱“由是勵志為圣賢之學,得明道程夫子‘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之語,佩服之,因以敬恕名堂,與同志會文講學”[2]自敘。耿介在成書于康熙九年(1670)的《省克錄自序》中對其思想轉變過程有更為詳細的說明:“弱冠習舉子業,揣摩帖括文藝,希世取寵,不知體貼身心為致知力行之地。既而謬博一第,濫竽史館,與睢陽湯孔伯同年。風雨晨夕,三閱寒暑,切琢之功為多,未幾補外。向之所得,乍明乍滅,若斷若續,雖宦海風波歷盡盤錯,然中無所主,動多窒礙,且是非無以辨,往往有認人欲作天理者,荏苒歲月,競成蹉跎。投閑以來,靜坐中讀程夫子‘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之語,佩服之。然斯道大,數年無入處。嗣得夏峰孫先生《理學宗傳》書,潛心玩味,方知我輩只為氣質拘定,便有無限病痛,所以張橫渠先生教人先須變化氣質。然我之病痛不能自知,都被圣賢一一道破,每有所觸,如晨鐘初覺,驚汗浹背。”[2]103從中不難看出,耿介對早年熱衷功名利祿頗為后悔,認為浪費了不少大好光陰。中年以后有心向學,卻一時不能得門而入,難以登堂入室,而這時孫奇逢所著《理學宗傳》便成為引領耿介進入理學殿堂的燈塔。
耿介得以正式拜入孫奇逢門下是由好友湯斌引薦,而耿介與湯斌定交則始于順治九年(1652)二人同在翰林院讀書時,耿介自敘稱:“壬辰,會試中詩四房二百三十三名……入翰林院讀書,教習老師,內院學士河陽薛公諱所蘊。舊例庶常入館,每人各一房,余與睢陽湯潛庵同年合并一房,朝夕以淡薄寧靜砥礪。”[2]自敘此后,耿介、湯斌二人雖然聚少離多,但一直書信往來不斷,交情甚篤。教習老師薛所蘊和孫奇逢也關系匪淺,早在順治二年(1645)就曾向朝廷舉薦孫奇逢,孫奇逢南遷到達輝縣后,最初的住所便是薛所蘊在百泉的別業。有理由相信,耿介在翰林院時期,或曾從薛所蘊處得知過孫奇逢的學行。
耿介和湯斌的書信往來及孫奇逢的《日譜》記載了耿介從動意到正式拜師的整個過程。康熙十二年(1673)初,耿介寫信給湯斌稱:“頃讀《理學宗傳序》,洞見道體粹然醇正,中原文獻之傳,微年兄其誰與歸?……但愚昧如弟,蹉跎半生,一事無成,遂已鬢為白。邇來貧病交侵,窮年杜門,惟有理義悅心,不至狼狽。然斯道大苦無入處,又離群索居,孤陋無似……夏峰先生,今之程朱也。弟仰企有年,未敢造次。祈年兄字,先容弟將遣使納贄受學,俟賤恙大可,然后策蹇蘇門,登堂執弟子禮耳。”[2]113耿介首先對湯斌的學問表示欽佩,然后請湯斌給孫奇逢寫信引薦,鄭重表達了欲拜入夏峰門下的心意。湯斌回信則稱:“前在蘇門,已久向征君先生言之,征君先生亦想慕豐采久矣。來教具見若虛之懷,使人佩服。弗諼如命敬草一函奉上,先生厚德古道,贄亦不必甚拘。”[2]114湯斌回信說之前已向孫奇逢說過耿介有意拜師之事,同時告訴耿介,孫奇逢厚德古道,拜師之禮不用太過拘泥。接到耿介信后,湯斌又特意寫信給孫奇逢:“敬有啟者,登封耿逸庵與斌壬辰同館,德性醇樸,學術正大,宦轍所至閩南豫章,皆有善政可紀。秉憲天雄,茹蘗飲冰,厘奸揚弊,士民謳歌,至今無斁。居家孝友,內外無閑言,其堅定之操,守禮之嚴,斌生平交游未多見也,相別十八年,時相夢寐。適接手書,云求教真篤,不啻饑渴,仰慕山斗,欲遣人納贄受學,俟病體大愈仍負笈蘇門,請益函丈。憶昔躬侍座右,言及中州人物,斌即首舉逸庵,以為此躬行實踐之士,真不易得。今歸依誠篤如此,伏望吾師鑒照,進而教之,吾道之幸也。”[2]114-115湯斌此信向孫奇逢說明耿介為官有善政,居家嚴守禮法,向學求教之心誠篤。
孫奇逢于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三《日譜》記載:“登封耿逸庵介湯孔伯書來問學。逸庵名介,以太史出為參副。自大名道丁艱歸,遂不出。其清操惠政,士民思之。孔伯素稱其好學。”[3]1290至此,耿介正式拜入孫奇逢門下。
二、孫奇逢與耿介交游的具體情況
耿介自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抵達夏峰,第一次向孫奇逢問學。據耿介二月八日在夏峰寄給湯斌的信中說:“念七日晚得手教并上征君先生書,批讀一過,頓使沉疴去體。遂于二十八日起行。至河干,大風不可渡,日已夕無投止處,向三家村借茅屋半間一宿。由柳園北渡,二月初二抵夏峰拜先生。蒙先生不棄,朝夕提命,聞所未聞。”[2]116耿介收到湯斌回信的第二天就啟程趕往夏峰村,可見其向孫奇逢問學的迫切心情。到達黃河南岸后又因為大風不能渡河,但耿介求學之心堅如磐石,在渡口附近村莊借宿一晚,于第二天北渡黃河,終于在二月初二抵達輝縣夏峰村。耿介見到孫奇逢后,“蒙先生不棄,朝夕提命,聞所未聞”,由是眼界大開,學問日進。此次問學,孫奇逢告誡耿介為學“功夫只要誠,要有恒,便無破綻矣”,并親自現身說法道:“吾只是貧病二字結果了一生,然極得貧病之益。貧豈能累人?疏食飲水,樂亦在中,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中滋味誰人嘗得出?能曉得貧病滋味,貧亦是道。病亦豈能侵人?……我輩只養得心靜時諸病自退,病亦是學。”[2]116
孫奇逢向耿介講述為學入道之途時說:“孔子獨以鄉愿為德之賊者,以其忠信廉潔皆出于偽也。時時照察,時時克治,務去其欺,務去其慊,方能日用倫常不離于道耳。學者起頭用力,要有李光弼入軍旌旗變色氣象。其既也,要有周亞夫中夜聞警堅臥不起定力,然后可以入道。”[2]116孫奇逢為學非常注重躬行實踐,他對耿介道:“學者只要躬行實踐。夫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又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皆是側重行。人誰不知忠君孝親?必須行忠君孝親底事。”[2]117
對于耿介的此次夏峰之行,二月初六孫奇逢的《耿逸庵臨路索手書》有記載,而耿介卻說二月八日在夏峰給湯斌寫信,不知是他們二人誰記載有誤,還是耿介“臨路索書”后又因事耽擱了幾天。孫奇逢在《耿逸庵臨路索手書》中寫道:“與君一河之隔,家居十載,曩從孔伯識其為學人也。遠承枉顧,虛懷下詢,數日來或口語相印,或手疏相質,具見近里著己知行并進之功,而君猶競競于氣質之未能變化,途徑之或有差失,此足以見君好學之切矣。仆嘗聞鹿伯順言學,說心在事上見,人有實跡,便學有實用。離事物而虛談性命,性命何著?外性命而泛言事物,事物何歸?公所云敬恕本體功夫,一齊俱到。變化氣質,須戒慎操存,久則不放,方能見活潑潑地,而氣質自能變化矣。事無棘手,從學無歇手來。君與孔伯為友,洛學之興,有厚望焉。”[3]1291孫奇逢對耿介“競競于氣質之未能變化,途徑之或有差失”表示贊賞,并具體論述了變化氣質的方法,認為耿介和湯斌可以承擔興復洛學的重任。《耿逸庵臨路索手書》也見于《敬恕堂文集》,題為《夏峰先生手書》,二者文字大致相同,最主要的區別在如下部分:“說心在事上見,說己在人上見,政有實跡,便學有實用。”[2]115此處,孫奇逢主要回答耿介關于如何修養身心的問題,他力倡實行,主張在實際的政治、事物上談身心修養。此后,受孫奇逢說法的啟發,耿介對理學與舉業的關系產生了新的認識。康熙十三年,他成立輔仁會,在《輔仁會約》中說:“古之學者,體用一原,所以性道、文章未判為二事。自科舉興,而體用稍分矣。雖竭畢生攻苦之力揣摩成熟,只是為文章用,語以性道則群起而疑之。詎知性道文章猶根本枝葉,根本不培,則枝葉不茂。馮少墟云:‘以理學發揮于詞章,便是好舉業;以舉業體驗諸身心,便是真理學。’……然則今日論學,正不必煩多其辭,只是于舉業上加一行字。”[2]140正是受到孫奇逢的影響,耿介才努力綰合理學與舉業之間的關系。
孫奇逢和鹿善繼為莫逆之交,耿介向孫奇逢問學時非常推崇鹿善繼,于是孫氏找出鹿善繼手跡并作題跋道:“逸庵論學,服膺江村。欲得其手跡,朝夕相對,如見其人焉。因簡篋中,有少年手錄唐詩一紙付之。筆墨有靈,精神相合,逸庵當不徒以字觀之。”[3]1291
康熙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孫奇逢作《懷友詩》稱:“廉幹推逸庵。”[3]1312十一月初二日《日譜》載:“答耿逸庵書,稿入集。”既然是答書,必然有耿介寫給孫奇逢的來信,可惜兩信都沒有保存下來。是年,耿介有《上夏峰先生書》:“恭惟先生:純粹性生,中和體具。元善充周,一身備四時之氣;太極渾灝,千春斂五福之祥。蓋艮止不遷,自得仁人之壽;而健行無息,允符天道之恒者也。今值紱麟之辰,不能躋堂介眉,盡弟子之誼,一芹將意,伏冀鑒存。”[2]118據《漢語大詞典》“紱麟”條釋義:晉王嘉《拾遺記·周靈王》:“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魯襄公之世……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文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征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系麟角,信宿而麟去。”后以“紱麟”為慶賀生辰之典。由此可知,耿介此信寫于十二月十四日孫奇逢生日之前不久,耿介此信除祝壽外還提到了年初夏峰之行的收獲和回家后的自學心得:“春來得摳趨函丈,承領提誨,復蒙手書開誘諄至,歸來日用間用省克功夫,變化氣質,因體吾師‘戒懼操存,久則不放’之語,乃知此是程門涵養,須用敬功夫也。朱子有言:‘人須是大原本上見的透。’介因于大處無所見,手輯《理學要旨》一編,朝夕涵詠潛玩,謬為小序,便中錄呈,其有不合理者,幸吾師指摘賜教,庶向往不致差錯耳。臨池不勝馳切之至。”[2]118孫奇逢的回信不見于《日譜》和《夏峰先生集》,幸運的是耿介的《敬恕堂文集》保留了這封珍貴的書信:“春日承枉顧山村,以夙昔景仰而不得見者。一旦辱折節禮下問,不能問寡于聾瞆蹣跚之老生,在使君高誼虛懷迥出塵俗,而仆之僭妄,誠有不可自喻矣。別后每懷想,素心馳情于兩室之麓,自念精力久頹,惓惓方寸所望于良友者,獨此共學一事。捧讀來札及《要旨》自敘,見地已明,擔荷甚力,晚年獲此,實慶同心,不勝拜服。仆嘗謂學問之道,原平鋪直敘,著落于日用倫常,無甚高遠難行,能于此中見得觸處皆天命流行,便是透得大原本所在,高明已到康莊,又何慮前途荊棘耶?佳稿即僭為評次,附便帶回。遙望停云,神與俱往。”[2]118-119
康熙十三年(1674)春夏之交,耿介本擬再次前往夏峰向孫奇逢問學,因故未能成行,為此致信孫奇逢道:“自客冬拜接手教,服膺無失。本擬今春夏之交負笈請益,竟以時事紛紜不果所愿,夢寐之間,如侍函丈,茲因便鴻,敬候萬福。為學之道,矢諸造次顛沛,雖未知后來如何,惟求功夫不間斷耳。拙詩一首,錄呈師覽,伏乞削正賜下。縷縷之私,尚容專布。不宣。”[2]120耿介此信再次談到為學之道需要造次顛沛而不間斷。孫奇逢的回信《日譜》未載,僅于七月十八日記有“復耿逸庵書,稿入集”一句,不知和耿介《敬恕堂文集》所附的孫氏回信是否同一封。孫奇逢回信稱:“入春,塵飛云擾,自念九十一歲人,惟求寧貼身心,不敢以倥傯閑度日,以睿圣抑詩為功課,益信學問全無止期,更無一毫放過處。恨蹣跚狼狽,不能請益同學,為燈光之助,然停云之思,無時不馳神嵩少間也。忽接手教,如覿眉宇。佳詩具見徹悟后語,第持此以往,自當有水窮山盡時也。頃聞東山將起,愛天下蒼生,何如愛天下頑懦?知己應同此意耳。”[2]120孫奇逢以自身為例,勉勵耿介為學要持之以恒,終生不懈,同時對耿介的治學路徑表示贊同。
推薦閱讀:文學專業類cssci刊物目錄
CSSCI也就是大家所說的南大核心,在國內核心期刊中影響力非常高,對稿件要求非常高,投稿上有一定難度,有投稿需求的可以聯系在線編輯。這里小編給大家整理了一部分關于文學專業類的cssci期刊,供大家參考。有投稿需求的,可以直接與期刊天空在線編輯聯系。
耿介《敬恕堂文集》有一封致孫奇逢四子博雅的回信,信息量很大,為便于分析,全文移錄如下:“囊追隨世兄伯仲間,得略觀老師《讀易大旨》,心欲攜來抄置幾案,朝夕展誦,以未有副本,逡巡未敢請。及歸,得別本反覆披讀,但斯道大,難得遽窺微妙,因竊自思,須得百泉山水間,侍函丈親承提命,一兩月或可少開茅塞,但此愿未能即遂,當俟異日。前捧接師諭,知福履勝常,甚慰于懷。重聞抑詩為功課已恍然,于出話威儀之間必敬必慎。頃復拜手教并日譜錄示,敢不益勉其所不逮以遵師訓哉?出處之際已內斷于心,蒙師教親切,益覺自信無疑。拙詩得吾師手書,當什襲藏之。附謝。山中頗靜,正宜讀書,但苦于孤陋,《周子通書》四十章于師友三致意焉。前侍坐師席,于良友切琢之益,亦不啻諄諄及之,一帶之隔,豈遂嘆其修阻!而瞻望芝宇,如天邊云霞,可望不可即,離群索居之感,豈不古今有同情耶?乘便奉復,兼候道履。馀情未盡。”[2]124-125此信后附錄有《夏峰先生書〈讀易詩〉后》一文,抄本《夏峰日譜》于康熙十三年八月十一日下恰好記有:“題逸庵《讀易詩》,稿入集。”由此推論,孫博雅(字君僑)在孫奇逢題《讀易詩》后給耿介寫信,而耿介《回孫君僑世兄書》或在是年八月中下旬寫定寄出。耿介信中提到很渴望能抄錄孫奇逢所著《讀易大旨》,因沒有副本,猶豫再三沒敢開口,回鄉后研讀易學著作,一時難登堂奧,渴望能再次前往夏峰問學。“出處之際已內斷于心”表明耿介已經絕意仕途,他的決定也得到了孫奇逢的贊同。山中環境安靜,很適宜讀書,可惜得書不易,為求《周子通書》,耿介再三向師友求援。耿介很渴望有良師益友可以切磋學問,大有離群索居之感。孫奇逢《〈讀易詩〉后》一文對耿介大加稱贊:“《易》與天地準,知《易》則知天地矣,故吾夫子欲假年以學,時中與《易》二名無二體也。逸庵(耿介)之言曰:‘既讀《易》之后,《易》在吾心。’此深于《易》者也。得此旨而學之不息,自有隨心應手之妙。《讀易》一詩,俱見徹悟,老夫不覺躍然欲起。”[2]125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