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6-05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日本在吸收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贈禮文化,禮物流動的深層邏輯是相互依賴的人際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終身雇傭制的衰落和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給強調共同體意識的日本社會帶來巨大沖擊,隨意的禮物社交禮物自我禮物等個人化禮
[摘要]日本在吸收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贈禮文化,禮物流動的深層邏輯是相互依賴的人際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終身雇傭制的衰落和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給強調共同體意識的日本社會帶來巨大沖擊,“隨意的禮物”“社交禮物”“自我禮物”等個人化禮物形式的興起表明日本社會的禮物流動和人際關系正朝著新的趨勢發展。從禮物饋贈的視角來看,當代日本社會的人際關系具有三個新的特征:(1)比起基于“義理”原則的“仲間關系”,當代日本人越來越重視基于“人情”原則的“身內關系”;(2)在互聯網時代,陌生人之間通過社交平臺建立起“電緣關系”;(3)隨著單身群體的不斷增加,個人與“自我”之間呈現出一種“異化關系”。
[關鍵詞]日本社會;贈禮文化;電緣關系;關系異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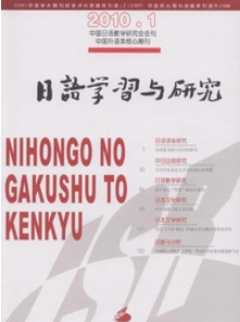
禮物饋贈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縱觀古今中外,無論是在公共關系領域還是私人關系領域,禮物都是人際交往的重要載體。贈送禮物時,不僅需要遵循一定的儀式和禮節,而且和人與人之間的親疏關系密不可分。
日本在吸收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贈禮文化:既重視東方式的禮尚往來,又奉行西方式的AA制原則。禮物能夠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AA制卻營造出互不相欠的距離感。日本人在人際交往中所呈現出的雙重特性,實在令人感到驚訝和疑惑,由此筆者聯想到列維-斯特勞斯曾經說道:“一直以來,日本思想具有很高的原創性,不僅迥異于我們(西方)思想,與其他遠東哲學相較也截然有別。”[1](p39)帶著這一疑惑,筆者試圖從禮物的視角來分析當代禮物饋贈的方式、動機和功能發生了哪些新的變化,進而探究當代日本人的人際關系具有哪些新的特征。
一、文獻綜述與分析方法
日本國內的禮物研究最早是以民俗學為中心來開展的,主要圍繞贈禮的契機、禮品的種類、禮節、社會關系、回禮方式等進行系統的民俗調查和資料收集。柳田國男認為,贈禮習俗源于神和祭神的人的共食現象,即禮物本來是給神的祭品,祭神之后,作為神的回禮,祭祀的人可以和神一起享用祭品。神人共食的現象后來逐漸演變為人與人之間互贈禮物。
20世紀70年代以后,各個學科領域開始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日本的贈答文化。別府春海從社會交換論的角度研究日本的禮物交換,他將贈禮契機分為“贈答(贈答)”和“物品交換(もののやり取り)”兩大類,并指出日本的禮物研究偏向“贈答”而較少關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交換”[2](p40-43)。伊藤干治和山口睦從人類學的角度出發,分別闡明了日本文化的贈答結構和贈禮行為背后日本社會的近代化及地域社會的變遷。山口睦發展了別府春海對贈禮契機的二分法,將近代日本的贈禮領域分為傳統的贈禮領域、個人的贈禮領域、公共的贈禮領域和國民的贈禮領域[3](p4)。
國外對日本禮物研究的專著相對較少。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首次使用“義理”“人情”的概念來分析日本人行為方式的特點,她指出,日本人對“義理”的報答在思想上是毫厘不爽,等量對待[4](p129)。關于日本的贈禮,巴特在《符號帝國》中寫道,“贈物者與受物者都為那件表示禮節的東西而相互施禮,那是個盒子,里面很可能什么東西也沒有,或者干脆說,空空如也。”[5](p101)他認為,日本人相互傳遞的禮物不過是一種空洞的符號而已。
目前國內對日本贈答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論文層面,內容多為日本贈答習俗的特征和禁忌、日本人送禮的文化心理以及中日送禮習慣的比較等等,涉及現代饋贈習慣的研究相對較少。王宇新在《日本年輕人饋贈行為考察分析》一文中比較了傳統饋贈行為與現代饋贈行為的特點與變化[6](p65-71),但他只做了概括性的對比,并沒有對饋贈行為發生變化的原因展開分析。
王夢琪在《現代日本贈答習俗的特征及其社會作用》一文中對現代贈答習俗的特征進行了歸類并對日本贈答文化的獨特性進行了分析[7(]p5-6),袁亦秋在《從贈答習俗看中日人際關系的特征》一文中試圖分析了贈答習俗所反映出來的中日人際關系的特征[8](p4-5),但她們沒有論及互聯網時代新的禮物形式和人際關系的變化。在本文中,筆者主要著眼于互聯網時代禮物饋贈方式、動機、功能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進而分析禮物背后所隱藏的人際關系的新特征。
馬林諾夫斯基、莫斯和薩林斯等人類學家在對禮物的功能進行分析時,都曾指出禮物的流動承諾或開啟了社會關系。在日本,禮物饋贈中的人際關系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遷而呈現不同的特點。在村落共同體和企業共同體的時代,贈禮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加強集團內的相互交流,強化成員的歸屬意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企業共同體的崩解和家庭結構的變化,脫離了企業和家等組織的個人贈禮活動開始活躍起來。
為了探究禮物饋贈的變化所折射出的人際關系特點,筆者以土居健郎對日本人際圈層結構的分析為依據,從個人與“親人”的關系、個人與“熟人”的關系、個人與“他人”的關系以及個人與“自我”的關系這四個層面來闡述不同類型的人際交往和禮物饋贈。土居健郎根據依賴和客氣的程度將日本人的人際關系分為三個層次,最里層的“身內”是一個全面依賴且無須客氣的人情世界;位于中間層的“仲間”是一個不敢過于依賴對方、彼此需要客氣的義理世界;最外層的“他人”是一個既沒有依賴關系也不需要客氣的陌生人世界[9](p47-48)。
日本的人際圈層結構和中國人由親人、熟人和生人構成的人際圈類似,但與中國人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的親人和熟人之間是不可轉換的,而日本的“身內”與“仲間”之間具有一定的可轉換性;二是中國的人際圈是以自己為中心向外擴張社會關系,而日本并不存在獨立于團體之外的自己,個體只是大小團體層層套疊的結果。在闡述日本三個人際交往圈的關系時,土居健郎進一步指出:“這三個范疇的界限并不是劃分得十分嚴格。
‘義理’和‘人情’也并非絕對相互對立,本應是充滿人情的親子關系會轉變成冷酷的義理關系,反之,無親無故的他人,也有可能跨進‘彼此相依’的關系圈內。”[9](p47-48)尚會鵬用“緣人”的概念來界定日本的基本人際狀態,并認為:“它(即‘緣人’)是由并非完全基于血緣關系而是基于包括其他因素的某種機緣(血緣、地緣、業緣或者其他因素)走到一起的個體組成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可轉換性和不確定性。”[10](p102)由此可見,日本的人際交往圈和義理人情的交往原則都不是絕對不變的,自我的確定和個人的行為主要取決于個人在當時當地的情境下與他者的關系,以下將針對不同人際關系中禮物的饋贈模式展開具體分析。
二、禮物的情感性饋贈:個人與“親人”的“身內關系”
以霍曼斯為代表的社會交換理論以理性選擇為原則,認為個體行動與否取決于成功與價值這兩個因素。這一理論以經濟交易做類比,忽視了行動者在交換活動中的情感投入。莫斯通過對古式社會夸富宴的研究證明除了等價的商品交換,還有另一種交換形式,即具有信用、服從、地位、崇拜等情感價值的“非對稱”交換。正如日本社會中“恩”“義理”“人情”等概念所表明的那樣,人與人之間通行的也是一種附帶了感情價值的交換模式。日本的贈禮習慣最初源于對神靈的敬畏和感恩,后來逐漸世俗化,發展為對關照過自己的人以禮物的形式表示感恩和答謝。
當這種感恩是出于個人自發的情感時,就是所謂的“溫暖的義理”,即義理和人情相融合。如果報恩的義理并非出于行為者的自愿,而是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規范,這就是所謂的“冰冷的義理”,即義理和人情相脫離。別府春海在對禮物的物質性贈予進行分類時,曾指出,中元、歲暮等傳統的贈答習俗以義理為原則,而日常的物品交換則是以人情為原則。
他認為,隨著日本社會迅速地現代化,送禮活動越來越個人化和工具化①。然而,根據矢野經濟研究所2009年針對個人禮物市場所做的調查顯示,在2000至2009年這十年間,以中元和歲暮為代表的“正式的禮物(フォーマルギフト)”②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而“隨意的禮物(カジュアルギフト)”③則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矢野經濟研究所2015年國內禮物市場的調查結果也顯示④,受少子高齡化、核家庭化以及地域、親屬關系的稀薄化影響,禮節性的贈答活動日漸減少,而對父母、孩子和好友表達感謝、好意和愛的禮物饋贈占據了主要的禮物市場,說明禮物饋贈并沒有越來越工具化,而是越來越注重個人情感的表達。日本的禮物市場之所以出現從“正式的禮物”到“隨意的禮物”的轉向主要是因為社會關系發生了改變。
在以終身雇傭制為基礎的企業共同體中,管理者和員工之間,員工與員工之間形成了長期穩定的“社緣”⑥關系。為了促進集團內的相互交流和強化成員意識,日本式經營的企業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在中元、歲暮時節向上司和與工作相關的人贈送禮物,既表達對日常關照的感謝,也包含各種功利的目的。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以后,終身雇傭制的衰退帶來“社緣”關系的淡化,企業內部員工給上司送禮的現象逐漸減少。此外,經濟的不景氣使得家庭收入變得不可預測,為了節省生活開支,人們不得不減少中元、歲暮的禮物開支。
不僅如此,中元、歲暮等傳統贈禮節日也呈現出隨意化的趨勢,過去主要是向幫助和提攜過自己的師長和領導,或是有合作關系的客戶送禮表達感謝和問候,現在的中元和歲暮則慢慢成為家人或親戚之間加強情感聯系的重要契機。這是因為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和社交網絡的興起,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往逐漸被間接交往所取代,通過在中元、歲暮互贈禮物能夠起到表達關心、增進溝通的作用。近年來,個人間的隨意性饋贈逐漸占據了禮物市場的主導地位,反映出禮物贈答的動機發生了轉變。傳統的贈答習俗以“恩”和“義理”為原則,目的是為了維系共同體內部的和諧關系;而個人間的隨意性饋贈則以“人情”為原則,目的在于表達自己的真心實意,屬于情感性饋贈。
以往的研究往往強調把人情看作一種可交換的資源或是理性計算的結果,閻云翔在《禮物的流動》中特意關注了人情的道德和感情方面,人在這里代表私人關系,而情是感情的意思,所以“人情”這個詞應當被理解為在感情基礎上的私人關系[11](p141-142)。日本的“人情”觀念和中國的“人情”一詞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共同之處在于它也是指個人的情感,代表著一種私人關系。區別在于日本的“人情”范圍比中國要窄,一般是指父子兄妹這類自然的血緣感情,即在“身內關系”的范圍內發生作用。超出了“身內”的范圍便是“義理”的觀念在發揮作用。個人與“親人”之間的“身內關系”強調的是“人情”,即肯定相互依賴,積極地接受對方的情感。而所謂的“義理”,實質上是人情關系的一種延續,它是把親人關系人為地拉入到熟人范圍的人際關系之中,比如一般的朋友、同事、鄰居等。
三、禮物的符號性饋贈:個人與“熟人”的“仲間關系”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贈禮活動“中元”“歲暮”和人生的重要儀式“婚禮”“葬禮”都屬于正式禮物的范疇。中元和歲暮都是源于祖先崇拜和神人共食的傳統節日。中元是將中國道教的中元節和佛教的盂蘭盆節相結合而形成的祭祀祖先的節日,進入江戶時代以后,盂蘭盆節作為民間儀式得以盛行,人們在拜訪親屬和熟人時開始贈送“盆禮(盂蘭盆節前送出的慰問禮)”,這種盆禮也叫中元。而歲暮是人們為了在新年祭祀祖靈而將所需要的供品在年底送往父母家中,和中元一樣,歲暮也是在江戶時代普及到日本人的生活中。
中元、歲暮最初的贈禮對象主要是父母,目的是為父母祈福消災,由于江戶時代商業的發達逐漸發展為向日常關照自己的人贈送禮物,在表達感謝的同時也希望維系一種持久的交往關系。中元和歲暮基本上不用回禮,收到禮物以后立即和贈禮者聯系傳達謝意,然后再寄一封感謝信就行了。通過書信的方式來表達對日常關照的感謝和對收到禮物的感謝,會讓贈禮者感到更加高興。如果受禮者實在想要回禮的話,返還的禮物一般是收到禮物價值的一半。
在日本,婚禮和葬禮的回禮通常也是收到禮物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莫斯在研究古式社會的夸富宴時提出:“回禮是義務性的,是被期待的,而且要和收到的禮物相當”[12](p54),本尼迪克特也認為對義理的報答(即回禮)必須等量對待。日本為什么存在象征性回禮(如“オウツリ”①“禮狀”②)和部分回禮(如“半返し”③)的現象,禮物交換的互惠原則是如何得以實現的呢?筆者分析主要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元、歲暮所送的禮物是對別人日常關照的回禮,所以不需要返還禮物。中元和歲暮送禮并不同于傳統禮物研究中“物與物的交換”,而是“關照與物的交換”。
社會學家濱口惠俊把日本人的交換模式稱作“好意優先型”④,例如,一個人(甲)判斷另一個(乙)人需要幫助,就將幫助提供給對方,獲得幫助的乙非常感謝,于是在送禮時節,以回禮的形式酬謝幫助自己的甲,并將這種關系持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甲并不一定有明顯的功利性動機,可能只是出于偶然的、對于他人是否需要幫助的主觀判斷。而乙對于從甲處得到的幫助(即恩惠)卻產生了送禮酬謝的心理。因此,乙的送禮行為其實是對甲的關照的一種回禮方式,這一過程已經完成了甲與乙之間“關照與物的交換”,因此甲可以不用再返還禮物給乙,只要用感謝信作為形式上的回禮即可。
第二,迫使受禮人回禮的“義理”意識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義理”從我國傳入日本后,江戶時代成為武士必須嚴格遵守的道德規范。二戰以后,隨著日本社會民主化的發展,傳統的“義理”意識對人們的束縛出現減弱的傾向,表現在贈禮習慣上便是“オウツリ”“お捻り”⑤這類象征性回禮的出現。別府春海將日本人的禮物交換細分為八種類型⑥,其中,關于回禮的方式可概括為以下四類:(1)過去接受過禮物,按等額價值的禮物返還型;(2)對接受的禮物給予形式上的返還型;(3)是(1)和(2)的中間型,即返還的禮物只是接受的禮物的一半或三分之一;(4)是(1)與(3)的中間型,即禮物返還的反復。[13](p62-64)其中,(1)是依據均衡原理的均等交換,(2)屬于象征性回禮,(3)是排除均衡原理的不均等交換,而(4)屬于循環的不均等交換。由于日本人屬于“向心式”思維,習慣站在對方的立場看問題,所以部分回禮的目的是為了減輕對方接受禮物時的心理負擔。
第三,回禮之所以不一定等質等量,是因為禮物交換的互酬性并不在于實際價值的對等,而在于符號價值的對等。禮物的首要價值在于“禮”,其次才是“物”,可以說禮節、禮儀等社會行為規范的意義,大于禮物的使用價值。更直接的是,禮物的焦點在于它的符號象征意義,而不是物質載體。巴特在對日本的送禮習俗進行考察時就曾指出日本人重視禮物的包裝是為了表達一種形式上的禮節,也就是說禮物的形式不過是一種禮節的符號而已。
任何形式的交換只有達到一定的平衡才會持續進行,如果交換物品的實際價值不相等的話,它一定是發生了價值轉換的過程,使看似不等價的交換實現了意義上的對等。日本人贈送“正式的禮物”的時間、內容、包裝、用語幾乎都是固定的,具有程式化的特點,這些固定的形式就是一個個符號,代表著禮節性的意義。
正式禮物的饋贈目的并非傳遞感情,而是為了遵守傳統的常規慣例,維系和諧的社會關系。這種類型的禮物饋贈一般發生在“仲間關系”的交往圈中,“仲間關系”是指相互認識或熟悉,有一定感情投注但不能過于依賴的關系,這是一個人為地把周圍的熟人當作家人來看待的義理世界。處于這個交往圈中的日本人,接受他人的禮物相當于接受他人的義理,也就等于背上了無形的債務,如果不返還的話就會被周圍人疏遠,不被集團和社會認可。在村落共同體和企業共同體的時代,以“正式的禮物”為代表的符號性饋贈對于維持共同體的確認體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此類贈禮活動要注意把握適當的尺度,否則容易陷入虛禮或形式主義。
六、結語
通過上述對禮物饋贈中不同人際關系的分析,我們發現日本人傳統的義理人情觀念、內外觀念和自我意識等均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義務性贈禮活動的減少和自發性贈禮活動的增長表明當代日本人更加注重情感性饋贈。社交網絡的發展拓展了人際關系的外延,打破了傳統“內”與“外”的明確界限,陌生人之間也能通過“好緣”和“電緣”建立起類似“身內”關系的聯系。以“自我禮物”為代表的新型禮物表明網絡時代加速了自我意識的發展,但過度的自由又會帶來個人的孤獨。
從禮物饋贈的視角來看,當代日本人的人際關系具有以下三個新的特征:(1)比起基于“義理”原則的“仲間關系”,當代日本人越來越重視基于“人情”原則的“身內關系”;(2)在互聯網時代,陌生人之間通過社交平臺建立起了“電緣關系”;(3)隨著單身群體的不斷增加,個人與“自我”之間呈現出一種“異化關系”。筆者認為,網絡時代的到來,促進了“隨意的禮物”“社交禮物”和“自我禮物”等個人化禮物形式的快速發展,對日本的傳統饋贈習慣和強調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心理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盡管個人主義的意識得到一定程度的張揚和發展,但日本人的存在方式從根本上來說仍然受到關系的主宰。
參考文獻:
[1][法]列維-斯特勞斯.我們都是食人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日]別府春海.文化的概念としての『贈答』の考察.伊藤幹治・栗田靖之編著『日本人の贈答』.日本:ミネルヴァ書房,1984.
[3][日]山口睦.贈答の近代[M].日本:東北大學出版會,2012.
[4][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M].江蘇:譯林出版社,2012.
[5][法]羅蘭・巴特.符號帝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6]王宇新.日本年輕人饋贈行為考察分析[J].日語學習與研究,2008(1).
相關刊物推薦:《日語學習與研究》(雙月刊)1979年創刊,是國內日語界權威性的綜合學術刊物,面向全國廣大日語教學工作者、翻譯工作者以及專門從事日本語言、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學者。選登國內外有關日語研究的學術論文,報道日語研究動態,發表翻譯研究論文,日本古典與現代文學對譯作品、經貿文章譯注以及漢語和日語比較研究文章。本刊自創刊以來,博得國內外專家權威的一致好評,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