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9-07-22所屬分類:科技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泡通村的精神空間是由宗族體系、信仰體系和生活實踐等復合構成的。進入新時代,不僅需要維系良善精神空間,也需要不斷更新精神空間的內容。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并不完全適用對泡通村精神空間的解讀。泡通村村落在其歷史進程中已經形成了它自身的發展邏輯,
摘要:泡通村的“精神空間”是由宗族體系、信仰體系和生活實踐等復合構成的。進入新時代,不僅需要維系良善“精神空間”,也需要不斷更新“精神空間”的內容。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并不完全適用對泡通村“精神空間”的解讀。泡通村村落在其歷史進程中已經形成了它自身的發展邏輯,村民間和諧要素是主要的。村民間雖也有斗爭,但也絕不是導致泡通村場域變遷的主要原因,泡通村場域的變遷宜是歷史及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關鍵詞:泡通村;精神空間;場域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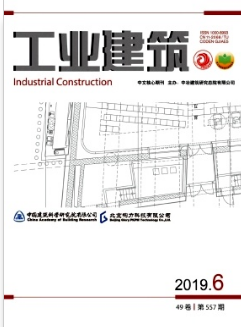
我國已進入新時代,正處于經濟轉型與發展的關鍵時期,國家大力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城市人口飛速增長,大部分傳統村落已變為城鎮。目前,中國西南地區,傳統村落仍然還大量存在。村落是指有一定數量的農業人群生活的聚居場所,也是一個世代生活、定居、繁衍在一定地域內農業人群的空間場域。在國家戰略指導和政策支持下,傳統村落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重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會產生出諸多新的發展思路和新的問題。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都對傳統村落展開研究,成果豐碩。
但是,國內學術界主要從傳統村落的價值、公共空間、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經濟、空間分布特征、村落保護等方面對傳統村落展開研究[1],對傳統村落“精神空間”的研究則心悟寥寥。布迪厄場域理論是當代較流行的理論之一,廣泛運用于社會學研究,但大都用之于某社會組織的研究,將其運用于微觀社區的成果卻不多。本文擬在場域理論的框架下,結合其他相關理論,對泡通村傳統村落作微觀研究,進而深化理論認知,反思理論觀點。
一、“精神空間”場域與泡通村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理論體系是后現代社會學的翹楚,影響深遠,很多著名學者都對布迪厄的理論作過評述。他的研究涵蓋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語言學、哲學、教育學、文學等領域。精神空間(thespaceofideologyorspiritualspaces)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講:人的行為是在空間中發生的,為了有效采取行動,人們需要心理表征空間,這與物理學家、幾何學家、繪圖師的空間構想是迥然不同的。
心理表征空間構建基于認知對象、宇宙萬物在認知坐標系中所呈現的空間關系等。不同的認知對象與所呈現的空間關系在不同的空間里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于是就產生了不同的心理表征,形成了空間內容[2]66-80,精神空間也稱之為心理場(MentalSpace)。這里講的精神空間也是指人對客觀事物認知的反應之后所形成的行動邏輯(理性與非理性的),它在一定場域里指導、規范、制約著人的行動。
在地理學磁場論的啟發及當代社會高度分化的時勢下,布迪厄在社會研究領域中提出場域(field)的概念。場域不僅是布迪厄社會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他說:“社會科學的真正對象也并非個體,場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須作為研究操作的焦點。”[2]146他認為:場域,“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2]134,正是這些位置的相對性構成了場域。布迪厄認為,場域應該是一個社會空間,而不是地理空間。
具體來說,就是大社會分化出來的一個個社會小世界,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各種不同的場域。如,政治場域、經濟場域、文化場域等。這些小場域構成了一個大場域———社會,是“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世界是由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的空間,而這些小世界自身所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約成支配其他場域運作的那些邏輯和必然性”[2]134。
布迪厄的場域還具有斗爭性和變動性的特征。布迪厄認為,“場域是力量關系———不僅僅是意義關系———和旨在改變場域的斗爭關系的地方,因此,也是無休止的變革的地方”[2]142。布迪厄從不把場域看成靜止不動的空間,場域內存在著各種活躍積極的力量。這些爭斗旨在維系與變更場域中力量的構型,正是由于它們之間不斷的“博弈”,不僅使場域充滿活力,還構成了場域發展的動力。“精神空間”場域概念,不僅受到布迪厄場域理論的影響,還受啟發于考夫卡及勒溫的“心理場”概念。
考夫卡認為,世界是心物的,經驗世界與物理世界不一樣。觀察者知覺現實的觀念稱作心理場,被知覺的現實稱為物理場,兩者并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人類的心理活動卻是兩者結合而成的心理場。心理場包括自我心理和環境兩個方面,環境又分為地理環境和行為環境,地理環境就是現實的環境,行為環境是構建的環境,受地理環境的調節;同時,有機體的心理活動是一個由自我———行為環境———地理環境等進行動力交互的場。
勒溫亦認為,“心理場”就是一種“心理生活空間”,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準社會事實———心目中的自然環境;2.準社會事實———心目中的社會環境;3.準概念事實———思想概念與現實的差異。”[3]泡通村是一個行政區劃,既可以說是政治文化的產物,也可以說是一個地理概念。泡通村村落文化沒有明顯邊界,但為研究考慮,現將泡通村視為一個場域區間,而在泡通村主域內,存在著大量子場域,這些子場域種類繁多,也沒有明確的界定標準。
如果以家庭為劃分標準,可分化出許多家庭子場域;以文化為標準,可劃分政治場域、經濟場域、信仰場域等;以可視形態為標準,則可劃分為可視性物理場域與不可視性精神場域。各場域間的關聯復雜,在泡通村特定場域內,可將它們之間的關聯概括為并列存在,相互影響。
二、泡通村“精神空間”體系構成
精神空間是相對于物理空間提出的。物理空間是由物質實體、社會實體所組成的可視性空間系統;精神空間則是指由人主觀建構的不可視性空間系統。兩者的關系,如同世俗空間和神圣空間的關系一樣,是一組二元對立關系。雖然,“精神空間”是人為構建抽象的空間系統,但“世間萬物,事實上,包括所有的社會與所有的文化,一如一臺機器,一個水晶體,都有其構成”[4]270。泡通村“精神空間”也有其相應的構成,包括宗族觀念、信仰文化、生活體系等。
十年前的泡通村是一個閉塞落后的村落,泡通村因泡桐樹而得名,其中居民大部分為謝姓,還有一小部分張姓、姚姓以及幾家其他姓氏,均為漢族。現有人口兩千多人,四百余戶,分為三個村民組:第一組位于姚郊,第二組位于茶樹坡,第三組位于落石巖。泡通村是一個典型的傳統農業村落,以水稻、玉米、小麥和大豆等為主要糧食作物,經濟作物有油菜、烤煙等,林副產品有茶葉,礦產資源有煤等。近年來,在黨和國家政策的幫扶和“打工經濟”的帶動下,泡通村的經濟呈較快發展態勢。村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交往空間范圍逐漸擴大①。
(一)源于宗族觀念的精神空間
宗族觀念是泡通村“精神空間”的主要因素。人類從原始社會開始,就以血緣締結關系,雖然之后隨著財富的私有與階級的出現,發展出以地緣關系締結的民族國家,但血緣關系仍是人類社會中最主要的關系,它也根植于中國文化之中。時至今日,人與人之間的親疏仍主要以血緣關系的遠近來界定,尤其是在村落中。“血緣所決定的社會地位不容選擇”;也“是穩定的力量,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生于斯,長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緣固定了”[5]72。
泡通村亦是如此,血緣近的,則關系親密,血緣較遠的,則相對疏遠,因之形成了一套因血緣關系不同而相互有別的親屬關系網絡,構成了泡通村“精神空間”的基礎,也即心理生活空間或心理場的基礎。“心理場”是一種“心理生活空間”,由“點”與“線”交替構成,“點”起著基礎作用。宗祠在村落中,是一個最核心的、具有正價的“點”場,是“心理場”的中心要素。泡通村宗祠,位于村落中央,規模較小,建于20世紀50年代,主要供奉謝姓先祖。
它不僅是后裔子孫追憶祖先的場所,還是泡通村謝姓居民弘揚禮法、監督族內事務的場所。每逢春節或重大節日,村落內所有謝姓村民都會集中于村落祭奠祖先。平時村內有大小活動,大部分也都是在宗祠內舉辦完成的。村民間有摩擦,也會在宗祠內解決。泡通村宗祠既是村民們日常生活的中心,也是他們“精神空間”的核心。其他村民個體或者家庭單位也是“心理生活空間”中的“點”。“線”也是此空間的重要部分,通過“線”鏈接著各個“點”,個體間的親屬關系就可視作一條線,家庭間親屬關系也可視作一條線。泡通村“心理場”正是一副由“點”和“線”交叉組合的場域視圖。
(二)源于信仰體系的精神空間
信仰體系是泡通村“精神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是“精神空間”,那么精神文化當然是重要組成部分,而信仰又是精神文化的主要要素之一。泡通村是一個漢族農業人群聚居的村落,信仰體系構成多樣化,主要包括祖先崇拜、原始宗教信仰、道教信仰及其他小眾信仰。祖先崇拜是中國自原始社會就普遍存在的信仰。泰勒(EdwardBurnettTylor)認為,祖先崇拜與“萬物有靈(animism)”理論相聯系。在原始人類的思維中,人在肉體之內或肉體之外還存在平時看不到,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被感知的另一種存在,即靈魂。人死的時候,靈魂會離開肉體,去往它該去的地方,靈魂不會死亡。人類靈魂觀念的產生,直接影響祖先崇拜信仰的出現[6]。
時至今日,祖先崇拜在許多國家依然存在,中國也不例外。祖先崇拜是泡通村村民最主要的信仰。以謝姓為例,崇拜的對象為其共同遠祖和各家支的嫡系祖先。祭祀方式為分家祭祀,即各自祭拜各自祖先,但九代以上的祖先不用祭祀。泡通村祖先崇拜中,祖先并非指所有的先人,供奉之先祖依賴于其子孫,子嗣尚存并有相應的祭祀儀式,祖先才具有以血緣為基礎之意義。
有些先民無子嗣,便無人祭祀,還有年幼夭折,犯大錯處死,死于非命的先人也無法享受祭祀,他們也不列入祖先序列。在泡通村村民靈魂觀念中,除存在良善的祖先靈魂外,還有邪惡的怨魂。早死、兇死等非正常死亡的死者,死后靈魂將不得安息,就會化為怨魂乃至惡鬼危害村民。每逢有村民身染惡疾、無故兇死,村民們都會將此類事情歸咎于惡鬼作祟。怨魂惡鬼不僅是成年人嚇唬小孩、規誡小孩行為的工具,甚至對成年村民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祖先崇拜具體表現為注重喪葬儀式。土葬仍是泡通村喪葬的主要方式。泡通村村民非常重視喪葬儀式、規程。他們認為,生者如沒有遵守這些儀式、規程,那就是對死者的不敬,死者的靈魂就不能安息,必化為怨魂惡鬼糾纏。反之,順利完成這套儀式,則象征著死者的靈魂順利地進入極樂世界,得以安息。這些儀式、規程由“先生”制定,“先生”是泡通村祖先崇拜的核心要素,許多祖先崇拜的相關儀式,如入土儀式、“慶壇”儀式、墳墓遷移儀式、墓地重修儀式等,都必須要由“先生”主持。
泡通村僅有一位曾姓“先生”,現年50歲,已司“先生”之職30余年,其業務范圍主要在泡通村,“先生”之職并非專職,其薪酬或以次數或以天數論計。2015年初,由泡通村村委牽頭,全體謝氏村民出資,重新修訂了族譜。族譜的修訂對團結謝姓族人具有重要作用。道教是中國人的宗教。幾千年來對我國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泡通村的村民們或多或少地繼承了道教文化的衣缽,主要表現于道教宮觀與生活習慣上。
道教宮觀是祭祀道教諸神的主要場域,也是精神寄托之所。泡通村有一座道教宮觀,規模較小,僅有一小間土木建筑,建于20世紀50年代,朝向西南,為懸山式建筑,屋頂的四角有青龍、白虎、玄武、朱雀四大神獸雕刻。殿上供奉道教原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玉皇大帝、真武大帝等十余位道教神仙。平時宮觀不對外開放,僅逢重大節日,如春節、諸神圣誕之日才會啟用。開觀之日,泡通村民及相鄰村寨的村民都會來進香求神保佑。由于宮觀面積較小,輻射范圍狹窄,該觀沒有專人管理,功能也不如其他大道觀齊全。
除道教宮觀外,泡通村道教建筑還有十余座土地廟,遍布泡通村各處。泡通村土地廟甚為簡陋,一般由幾塊石板搭建而成。廟內有泥塑土地公神像,居民們修建土地廟的目的是驅逐惡鬼,保護土地,以求莊稼有好的收成。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皆有村民會前去祭奠土地公。除祖先崇拜、道教及土地信仰外,泡通村還有其他的一些信仰,如佛教信仰、自然崇拜等。佛教教義如輪回、因果報應等概念深刻影響著村民的精神空間。佛教在泡通村及其周邊村寨并無廟宇,只有一些虔誠的農戶人家在家中掛有佛像,每逢佛教節日敬佛布施,以洗刷罪責與祈求庇護。
自然崇拜主要表現于對村里的一棵百年大桂花樹的敬畏崇拜。其樹位于村中央,每到農歷八月,村中彌漫著桂花的香氣,沁人心脾。偶爾也會有村民在中元節的時候給桂花樹上香、叩拜。還有一些奇形怪狀的巨石,被村民視為禁忌。村內長輩總會告誡孩子們不要去觸碰,說石頭里藏著吃人的山鬼,以警示孩子們嬉鬧游玩時要注意安全。小孩深信不疑,并代代相傳。這些信仰在泡通村和諧共存,共同構成泡通村信仰體系,也是其“精神空間”的一部分。
(三)源于生活實踐的精神空間
場域理論注重社會場域,卻忽視了心理的作用,行為環境論和生活空間論則強調主體的心理作用,忽視客觀環境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源于人們對客觀事物的反映。因此,“精神空間”不僅受主體心理作用的影響,也應受客觀環境,即生活體系的影響。“構成夢內容的所有材料在某種程度上都來源于體驗,也就是說,他們在夢中被再現或被憶起———至少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7]
22夢的內容來源于生活,那么,生活實踐也就構成了“精神空間”內容。生活環境對村民“精神空間”的建構有著重要的影響。居民日常的生活內容,如生產實踐、社會活動及節慶娛樂等直接影響其“精神空間”的建構。筆者曾訪談過村內兩名同齡青年,其中一位生活在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親屬網絡健全而復雜,家族在村內有一定名望,是在村民的呵護下長大,他認為,親屬關系及和諧的村民關系非常重要;而另一位青年,其父早亡,也沒有叔伯兄弟,與母親相依為命,在他的認知中,人生大都是圍繞自我和母親的內容。
因此,泡通村人精神空間的主要內容不僅有代代相傳的精神積淀,也離不開他們的生活實踐。在當代社會,也離不開與之息息相關的政治生活。過去,泡通村村民們有自己管理的一套鄉規民約,村落與政府聯系較少,村落的發展主要圍繞自身的鄉規民約。今天,村民的政治參與越來越多,意識不斷增強,也非常關心時政。村民們聊天的內容大到包含他們對政府政策的認識、小到對村內事務的關注。村民“精神空間”構成中,政治生活的比重越來越大。
泡通村“精神空間”場域的構成受到歷時與共時之諸多因素的影響。過去,泡通村的交往空間僅限于本村及周邊相鄰村落。如今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打工經濟”及互聯網的出現,村民的交互空間不斷擴大。因此“精神空間”也在“擴容”,不斷豐富。
三、良善“精神空間”更新與維系
“精神空間”有其自身的運行邏輯,尤其倡導良善要素。在不受外部條件的影響下,“精神空間”能夠通過本身的運行邏輯發揚良善要素,扼制不良要素。泡通村過去受外界影響較小,在不斷地調試中構建出具有積極和諧的良善“精神空間”。這種良善的“精神空間”很好地維系了泡通村的發展。良善“精神空間”中所包含的倫理道德、忌諱規則會約束村民的行為,引人向善;良善“精神空間”能夠凝聚力量,為村落的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增強村民的凝聚力,維護村落和諧。泡通村形成的良善“精神空間”多年來維護并引導泡通村不斷發展。
村內鮮有犯罪案件和民事糾紛,村民間和諧共處。2014年,鄉政府為發展考慮,號召各村寨集資,用于修整公路。泡通村村民對此事展開了討論,大部分人響應此決定,出錢出力,幾個月內就將村內的公路修整完畢。現在,許多村民都享受著交通帶來的便利。如村民開始將摩托車、小型貨車等用于農事勞動,既節約了人力,又提高了效率。許多村民還乘交通之便利,開始經營養殖業,或養雞,或養牛,泡通村的經濟也蓬勃發展。正是在這樣的選擇中,泡通村“精神空間”內容被更新,繼續發揚著其中的良善要素。因此,政府在主導精神空間建設方面的作用會越來越重要,影響會越來越大,對精神空間的架構與核心內容的更新會起主導作用。
四、結語
泡通村的“精神空間”是由宗族體系、信仰體系和生活實踐等復合構成的。進入新時代,不僅需要維系良善“精神空間”,也需要不斷更新“精神空間”的內容。本文主要以布迪厄場域理論為指導,分析了泡通村的“精神空間”。實際上,布迪厄龐大的思想體系中還強調反思性,反思的核心觀念便是對象化的對象化,在反思二元對立的方法論中,提出其實踐理論。正是秉持布迪厄的反思理論主張辯證對待其場域理論,并運用于泡通村微觀社區精神空間的探討與研究。然而,筆者認為,場域理論中的某些理論觀點并不一定適用對泡通村“精神空間”的解讀。
如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中強調斗爭、強調權力資源,認為進步正是在不斷競爭中進行的[8]52,但這卻不適用于這里的實際情況。泡通村村落在其歷史進程中已經形成了它自身的發展邏輯,村民間和諧要素是主要的。村民間雖也有斗爭,但也絕不是導致泡通村場域變遷的主要原因,泡通村場域的變遷宜是歷史及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現代社會日新月異,傳統村落在此背景下,正在經歷著重構的變革。泡通村是眾多的傳統村落之一,具有大部分傳統村落的共同特征。因此,對泡通村“精神空間”分析,可推演其他傳統村落,對如何構建新時代傳統村落的“精神空間”具有積極意義;同時,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堅持實干興邦,始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9]是傳統村落精神空間建設的指南針。
參考文獻:
[1]畢曉莉,楊仕恩,劉奔騰.近十年來國內傳統村落研究的成就[J].工業建筑,2016(10).
[2]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論[M].李康,李猛,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3]劉沛林.論中國歷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間”[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1).
[4]ClaudeLévi-Strauss.StructuralAnthropology[M].BasicBooks,Inc,1963.
[5]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
建筑類刊物知識閱讀:工業建筑雜志怎樣投稿
工業建筑是中國建筑科學方向的核心期刊,適合于土木工程界廣大科研、設計、教學、施工等專業技術人員及大專院校師生投稿,投稿錄用比例在55%,主要征收建筑設計、建筑結構、地基和基礎、建筑材料、施工技術等方向的內容,那么工業建筑這本核心期刊怎么投稿?投稿難度大嗎?其實只要您掌握了相關投稿技巧,順利投稿工業建筑期刊也是很容易的。
SCISSCI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