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5-12-17所屬分類:法律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正確認(rèn)識我國對文物保護(hù)管理的新條例措施有哪些呢,應(yīng)該從哪些方面來促使現(xiàn)在發(fā)泄的新應(yīng)用呢?本文是一篇法學(xué)管理條例。文章從縱觀現(xiàn)有法律體系,不難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條文均未對其行使條件進(jìn)行只言片語的規(guī)定。因而對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條件的構(gòu)建,
正確認(rèn)識我國對文物保護(hù)管理的新條例措施有哪些呢,應(yīng)該從哪些方面來促使現(xiàn)在發(fā)泄的新應(yīng)用呢?本文是一篇法學(xué)管理條例。文章從縱觀現(xiàn)有法律體系,不難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條文均未對其行使條件進(jìn)行只言片語的規(guī)定。因而對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條件的構(gòu)建,是解決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中困境的關(guān)鍵,也具有緊迫性。我們在構(gòu)建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行使條件時可以結(jié)合“出賣人將標(biāo)的物出賣于第三人”、“同等條件”、“行使期限”的共性行使條件,圍繞上一部分對行使時間點的研究結(jié)果,對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行使條件進(jìn)行構(gòu)建,為今后立法修改提出建設(shè)性的意見。
摘要:隨著我國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與國民文化生活質(zhì)量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出現(xiàn)了文物收藏的熱潮。然而,全世界藝術(shù)品的不法交易在暴利驅(qū)使下規(guī)模日趨龐大,這種畸形繁榮的背后卻是國家文化財產(chǎn)日益嚴(yán)重的流失和毀壞。人們逐漸認(rèn)識到,只有國家對文化財產(chǎn)的擁有優(yōu)先權(quán)利才能切實有效地保護(hù)好重要的文化財產(chǎn)。于是,國家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便應(yīng)運而生。不過,由于目前法律規(guī)定過于籠統(tǒng),我國的國有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在具體拍賣中如何行使產(chǎn)生了諸多的疑難,引起社會各界的爭論。下文中,筆者嘗試對此司題進(jìn)行一些個人的探究。
關(guān)鍵詞:文物管理制度,法學(xué)發(fā)展促使,法學(xué)管理條例
一、對國家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現(xiàn)有法律條文的理解
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又稱為先買權(quán)、優(yōu)先承買權(quán)、優(yōu)先承受權(quán),是指特定的民事主體基于法律規(guī)定或合同約定,在出賣人出賣財產(chǎn)權(quán)于第三人時,享有在同等條件下優(yōu)先購買該項特定財產(chǎn)的權(quán)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之存在,在人類法制史上已有悠長年代,尤其在中華法系中,自唐宋以后,尤見流行。目前,我國的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制度分散在各類法律淵源之中,除本文所討論的國家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制度外,還有共有人優(yōu)先購買權(quán)、承租人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合伙人優(yōu)先購買權(q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股東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等等。
法學(xué)論文網(wǎng)推薦:《法學(xué)研究》,《法學(xué)研究》刊載有關(guān)中國[法治建設(shè)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論文。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辦刊方針,堅持學(xué)術(shù)性、理論性的辦刊宗旨,堅持高水平的用稿標(biāo)準(zhǔn),以展現(xiàn)我國法學(xué)理論最新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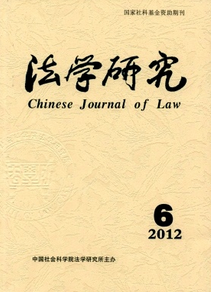
我國現(xiàn)行法律中涉及國家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條款有兩條: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hù)法》(以下簡稱為《文物保護(hù)法》)第58條,“文物行政部門在審核擬拍賣的文物時,可以指定國有文物收藏單位優(yōu)先購買其中的珍貴文物。購買價格由文物收藏單位的代表與文物的委托人協(xié)商確定。”另一為《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guī)定》第16條,“國家對文物拍賣企業(yè)拍賣的珍貴文物擁有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國家文物局和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文物行政部門可以要求拍賣企業(yè)對拍賣標(biāo)的中具有特別重要歷史、科學(xué)、藝術(shù)價值的文物定向拍賣,競買人范圍限于國有文物收藏單位。”
一般認(rèn)為,這兩個法律規(guī)定在行使時間與行使方式上產(chǎn)生了“法條競合”的狀況。依《文物保護(hù)法》第58條,行使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時間在拍賣前,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行使方式是文物收藏單位代表與拍賣委托人雙方協(xié)商。而《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guī)定》第16條規(guī)定的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時間為拍賣中,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的方式是舉行定向拍賣,由國有文物收藏單位以競買人身份參加競買。于是,根據(jù)“新法優(yōu)于舊法”、“上位法的優(yōu)于下位法”的原則,在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的場合,《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guī)定》第16條已經(jīng)不能適用,只有《文物保護(hù)法》第58條是目前國家對珍貴文物行使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合法依據(jù)。這種觀點有一定的瑕疵。“新法優(yōu)于舊法”是同位階法條間競合的處理原則,而“上位法優(yōu)于下位法”是不同位階法條間競合的處理原則。《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guī)定》的制定主體是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hù)法》的制定主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二者本來就是不同位階的法律規(guī)范,如果二者真的不能同時適用,就只能采用“上位法的優(yōu)于下位法”法條競合處理原則將《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guī)定》16條的定向拍賣規(guī)定予以排除。
不過,雖說《文物保護(hù)法》58條與《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guī)定》16條在行使方式和行使時間上有不同規(guī)定,似乎產(chǎn)生了法律沖突,但實際二者是可以并存的。《文物保護(hù)法》第58條規(guī)定的“拍前協(xié)商模式”與《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guī)定》16條規(guī)定“拍中定向拍賣模式”二者的確有著不同的法律效果,然而這兩種法律效果并不互相排斥。因為二者在前提條件和行為模式上只是部分重合,《文物保護(hù)法》第58條規(guī)定的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方式為“協(xié)商”,這說明這種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只是提供了一個先行交易的機(jī)會,而非是強(qiáng)制交易。在這種行使模式下,雙方僅能在意思自治的基礎(chǔ)上就合同締結(jié)的事宜進(jìn)行磋商,而并非像其他優(yōu)先購買權(quán)一樣,擁有對抗第三人效力,強(qiáng)行締結(jié)合同。再者,由于二者在行使時間上也有著不同的規(guī)定,實踐中完全可以在拍賣前先以協(xié)商形式行使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若協(xié)商未果再以“定向拍賣”的形式行使其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對于此,法律也沒有加以禁止,如果相關(guān)文物收藏單位如上述所言先后兩次行使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很難認(rèn)定此舉是否屬于超越了法律賦予的職權(quán)。
事實上,之所以產(chǎn)生以上觀點,主要原因在于定向拍賣曾在實踐中產(chǎn)生過諸多的弊端。拍賣能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標(biāo)的(文物)價值的最大化和資源分配的合理化(文物只有在自身經(jīng)濟(jì)價值被充分發(fā)掘后才會得到最好的保護(hù));但定向拍賣一方面使許多非定向范圍內(nèi)買家的競買權(quán)被剝奪,另一方面由于國內(nèi)文物保護(hù)資金嚴(yán)重匱乏,有資格參與競拍的文博機(jī)構(gòu)出價空間往往很狹窄,加之指定國有文物收藏機(jī)構(gòu)進(jìn)行競購時缺乏競爭拍賣機(jī)制,以至于拍賣成為了一個走過場形式。基于以上定向拍賣的弊病,多數(shù)學(xué)者急于將這一行使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模式排除在現(xiàn)有法律體系之外。不過,即使定向拍賣有著這樣或者那樣的缺陷,定向拍賣的設(shè)立初衷還是好的。在避免珍貴文物藝術(shù)品流入海外,在需緊急保護(hù)我國優(yōu)秀的文化遺產(chǎn)時,定向拍賣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筆者認(rèn)為,在現(xiàn)行的法律制度下,《文物保護(hù)法》與《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guī)定》規(guī)定的兩種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模式仍然有并列或選擇使用的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的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在實務(wù)中除了有“拍前協(xié)商模式”與“拍中定向拍賣模式”外,還有一種“拍后先得模式”。此模式源于2009年“春拍”中“中國嘉德2009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第2833號拍品“陳獨秀等致胡適信札”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先例。在該案例中,國家文物局參考了國外一些國家在文物拍賣中的做法,在拍賣前向拍賣人中國嘉德發(fā)出通知函,通知其將在拍賣后依據(jù)成交價考慮是否行使優(yōu)先購買權(quán)。此舉可謂突破了現(xiàn)有法律授權(quán)的范圍,在法定的職權(quán)之外“自我設(shè)權(quán)”,與行政法定原則相違背,是逾越行政權(quán)邊界的行為,應(yīng)當(dāng)作無效處理。我國屬于成文法制國家,在行政執(zhí)法中也沒有遵循先例的原則,所以相關(guān)行政主體不宜再以此方式作為先例行使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 三、對國家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現(xiàn)有行使制度的完善
從上述內(nèi)容可以推知,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行使之所以引起諸多爭議,其實都可歸咎于現(xiàn)行《文物保護(hù)法》關(guān)于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規(guī)定過于模糊。另外,更重要的一點是,現(xiàn)行法律體系中并沒有的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時間、行使方式進(jìn)行任何規(guī)定。致使相關(guān)權(quán)利主體在行使上有著很多的隨意性。但鑒于構(gòu)建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條件的涉及到背后各種利益的博弈,周期過長,欲要滿足現(xiàn)今愈發(fā)復(fù)雜的實踐需要,我們應(yīng)當(dāng)在未來修改《文物保護(hù)法》或《文物保護(hù)法實施條例》時,優(yōu)先在以下方面對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具體行使條件予以明細(xì)化。
(一)明確行使主體
關(guān)于國有文物優(yōu)先權(quán)的行使主體,《文物保護(hù)法》58條規(guī)定為經(jīng)國家文物行政部門指定的國有文物收藏單位。依《文物拍賣管理暫行規(guī)定》16條的規(guī)定,行使具體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主體是“國有文物收藏單位”。兩者雖然都將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行使主體規(guī)定為“國有文物收藏單位”,但仍然是極為模糊的。因為,我國現(xiàn)有的國有文物收藏單位數(shù)量龐大,分布極廣。如果國有文物收藏單位之間就同一標(biāo)的物同時行使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現(xiàn)有法律條文是無法找到解決途徑的。當(dāng)不同級別的文物收藏單位對同一文物要求行使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處理時,或當(dāng)同一級別的文物收藏單位對同一文物要求行使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處理時,便會產(chǎn)生“優(yōu)先購買權(quán)權(quán)利競合”的情況。這更會引起文物收藏單位是否存在級別越權(quán)、地域越權(quán)乃至事務(wù)越權(quán)的疑司。
另外,權(quán)利主體不明確將會為權(quán)利主體濫用權(quán)利提供空間,倘若文物收藏機(jī)構(gòu)財力不濟(jì),卻依然行使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時,不但對交易效率形成了阻礙,法律如何保障出賣人的利益也成為棘手的難題。因此,在將來的立法修改中,必須明確權(quán)利的行使主體,且增加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競合處理的程序性條文。筆者認(rèn)為,為徹底杜絕多個國有文物保護(hù)單位同時行使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可考慮將優(yōu)先購買權(quán)收歸國家文物局統(tǒng)一行使。設(shè)立專經(jīng)費,把其納入財政預(yù)算,以此保障該權(quán)利的有效行使。
(二)細(xì)化行使對象
細(xì)讀《文物保護(hù)法》58條,可知國家的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行使對象是“珍貴文物”,顯然過于籠統(tǒng),相應(yīng)行使主體無疑有較大的自由度。根據(jù)《文物保護(hù)法》第3條規(guī)定:“歷史上各時代重要實物、藝術(shù)品、文獻(xiàn)、手稿、圖書資料、代表性實物等可移動文物,分為珍貴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貴文物分為一級文物、二級文物、三級文物。”文物以其存在形態(tài)可以分為不可移動文物和可移動文物,依據(jù)《文物保護(hù)法》58條規(guī)定,可以得知行使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對象是可移動文物,但作為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對象“珍貴文物”究竟有沒必要涵蓋到三級珍貴文物,實在值得深思。況且,文物鑒定本來就極為復(fù)雜,直至現(xiàn)在還沒有一套得到普遍認(rèn)同的鑒定方法或可靠的科學(xué)儀器來鑒別文物真假。現(xiàn)有的文物鑒定多憑經(jīng)驗來鑒定,“即使是著名的專家、權(quán)威,其鑒定結(jié)果也不能作為‘終審’,往往幾位專家鑒定就會有幾種說法”。盡管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在館藏文物的認(rèn)定與定級上,國家已經(jīng)建立了相對完整的制度,但在民間收藏文物的認(rèn)定與定級上,現(xiàn)有的規(guī)定體系仍較為粗略。2009年的《文物認(rèn)定管理暫行辦法》及《關(guān)于貫徹實施<文物認(rèn)定管理暫行辦法>的指導(dǎo)意見》對民間收藏文物的認(rèn)定有所規(guī)定,但考慮到民間收藏文物認(rèn)定工作的繁巨性,這些規(guī)定的付諸實施還需要更多的配套制度,尤其是建立一套完善監(jiān)督機(jī)制。
有鑒于此,明確拍賣中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行使對象,必須改變當(dāng)前滯后的民間文物鑒定、估價等社會服務(wù)體系,這是從根本上解決拍賣中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對象不明司題的先決條件。一旦這一更大司題得以解決,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對象細(xì)化的司題便能迎刃而解。
三、國家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條件的構(gòu)建
目前,理論界對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應(yīng)如何行使的討論,其焦點主要集中在三種拍賣模式的優(yōu)劣與選擇上,這種思維定勢并非是解決司題的根本路徑。若要完善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行使制度,筆者認(rèn)為應(yīng)該以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理論的共性為切入點,對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行使制度進(jìn)行整體探討。
(一)文物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行使的最佳時間點
經(jīng)濟(jì)學(xué)上,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假設(shè)一個人是理性做出選擇的。而在現(xiàn)代民法領(lǐng)域,學(xué)者們也以私法自治為其基礎(chǔ),將“理性經(jīng)濟(jì)人”或“自由意志”作為大前提,假定當(dāng)事人能“依照自己的理性去判斷、設(shè)計自己的生活,并掌管自身的事務(wù)”。不過,作為民法上的一項制度,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卻對出賣人處分其權(quán)利的自由意志進(jìn)行了限制,賦予優(yōu)先購買權(quán)人優(yōu)先于第三人購買的權(quán)利,可謂在一定程度上偏離民法自由平等與意思自治價值目標(biāo)。歸根結(jié)底,這是法律在平衡特定的價值或利益時而有意做出的取舍。但是這種做法始終會留有權(quán)利濫用的空間,因此法律除在保護(hù)權(quán)利人優(yōu)先購買利益之外,必須同時兼顧出賣人的處分利益及第三人的競買利益。于是平,“出賣人將標(biāo)的物出賣于第三人”、“同等條件”、“行使期限”等限制條件被相繼創(chuàng)建出來,這就是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行使條件。優(yōu)先購買權(quán)在我國法律條文中通常表述為“轉(zhuǎn)讓人在出賣或轉(zhuǎn)讓特定標(biāo)的時,某某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yōu)先購買的權(quán)利”。可見,盡管各類優(yōu)先購買權(quán)自身有其特別規(guī)定,但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絕對是有共性條件的。而“出賣人將標(biāo)的物出賣于第三人”、“同等條件”、“行使期限”這三大典型行使條件就是優(yōu)先購買權(quán)的共性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