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5-07-06所屬分類:文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當前春樹小說的閱讀及對于現(xiàn)在的影響有哪些,如何看待春樹小說,它的作品中又體現(xiàn)了哪些觀點,對于這些觀點又該怎么理解和看法呢?《福建文學》是福建省最主要的文學月刊,由福建省文聯(lián)主辦,創(chuàng)刊于1951年。其前身為《園地》、《熱風》和《福建文藝》,1980年
當前春樹小說的閱讀及對于現(xiàn)在的影響有哪些,如何看待春樹小說,它的作品中又體現(xiàn)了哪些觀點,對于這些觀點又該怎么理解和看法呢?《福建文學》是福建省最主要的文學月刊,由福建省文聯(lián)主辦,創(chuàng)刊于1951年。其前身為《園地》、《熱風》和《福建文藝》,1980年改為《福建文學》。現(xiàn)任社長曾章團,執(zhí)行主編郭志杰,副主編劉志峰,編輯部主任賈秀莉,主編助理石華鵬,發(fā)稿編輯陳健、林芝、楊靜南、林東涵,美術編輯楊畋畋,責任總校潘越。
摘 要:若要分析村上春樹小說乃至整個日本小說的特殊性,毫無疑問,得從日本現(xiàn)代化的進程入手。與其他亞洲國家不同,日本并不是被動地接受外國文化,而是積極改造西方的先進文化,為己所用。這一點在村上春樹本人那里,展露得更為明顯。長期以來,整個日本文學就充斥著“回歸”與“前進”的矛盾,一部分作家愿意堅定地追溯先輩,一部分作家則一味地模仿西方。但有一點基本一致,那就是自明治時代以來,日本人在文學上普遍強調(diào)對個人主體意識的關注,這對村上春樹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關鍵詞:春樹小說,藝術來源,文學藝術
在村上春樹看來,喪失了個性和自由的女性,遲早會蛻變成物的奴隸、男人的附庸。村上春樹的青春小說,是帶有所謂“小資情結”的,這絕對是對女性的極大體恤。因為他知道,只有女性,才能撥動生活最純真、最細膩的那根琴弦;只有女性的意識得以覺醒,才算是真正實現(xiàn)了個體的自由。
一、村上春樹小說創(chuàng)作的藝術來源
眾所周知,日本文學自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之后,長時間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直到《挪威的森林》問世,日本文壇才有了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小說鬼才”,他便是村上春樹。去年,小說《1Q84》以其繁復而離奇的情節(jié)、成熟而精巧的技巧,再一次讓村上及其青春小說,進入了國內(nèi)外學者的研究視野。
1、村上春樹與美國文學
毫無疑問,村上春樹的小說創(chuàng)作受到美國文學的極大影響。美國文學慣有的荒誕感、幽默感,在村上春樹小說中體現(xiàn)得十分明顯。日本學者三浦雅士在論著《村上春樹和柴田元幸的又一個美國》中,就曾立論鮮明地提出,村上春樹的作品具有強烈的“美國文學的感覺”。上世紀末,諸多日本學者又先后從浪漫主義、存在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角度,對村上春樹的作品展開了分析,其結論無一例外地指向了美國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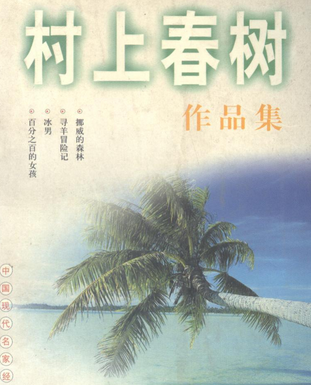
一部文學作品、一位作家的成功,與其所處的文化環(huán)境、文學傳統(tǒng)有關,但最核心的因素,必然是其強大的思想性、獨特的藝術性,村上春樹的作品即是如此。當我們以一種異樣的眼光去解讀《挪威的森林》時,我們所得出的觀點便不再理性、客觀。毫無疑問,村上春樹的小說有著強烈的人文色彩和獨特的個性,無論是人物刻畫,還是創(chuàng)作風格,都打破了人們對日本傳統(tǒng)文學的印象。村上春樹是一位不拘一格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歐洲的浪漫主義精神與“存在主義”立場,也看到了美國式的“個人救贖”,可以說,村上作品的復雜度遠遠超過了當下日本的任何一位作家,幾乎達到了這個時代“自我意識書寫”的巔峰。
縱觀整個19世紀的美國文學,總的感受是:悲觀主義大肆蔓延,而且愈演愈烈。很多美國作品受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影響,在敘述現(xiàn)實的時候,大多堅持回避的態(tài)度,這樣一來,作品的現(xiàn)實性減弱了,而追問內(nèi)心的精神性增強了。譬如村上春樹本人十分喜愛的兩部美國小說——《白鯨》與《了不起的蓋茨比》,就充滿了深刻的反思,以及無休止的絕望。小說中的人物和《1Q84》一樣,身處都市文明的重壓之下,身體和心靈早已失去了抵抗。受到這一類型作品的影響,村上春樹的部分小說就明顯表現(xiàn)出一種“厭世”的情結,甚至還夾雜著一些擺脫“恥感文化”、實現(xiàn)精神自救的復雜訴求。
村上春樹從事創(chuàng)作的那段時間,正是日本向后工業(yè)社會過渡的重要時期,也是各種文藝思潮風起云涌的時期。在這樣的氛圍下,可以吸收的文化養(yǎng)分很多,也很雜,很多作家往往迷失在西方文學的“萬花叢”中,找不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定位。村上春樹則不同,他及時從“盲目汲取的怪圈”里走了出來,在自己美國式的創(chuàng)作感覺中,融入了一許現(xiàn)實的苦悶與想象的怪誕。同時,他在人物塑造上另辟蹊徑,為小說的主人公們貼上了“憂郁”和“孤獨”的標簽,以引發(fā)青年一代的強烈共鳴。這樣,村上春樹就實現(xiàn)了對同輩作家的第一次超越。
2、村上春樹與傳統(tǒng)日本文學
村上春樹的小說之所以杰出,一方面在于靈性的模仿,另一方面在于對自我的認同。一個人的自我認同感,是建立在民族認同感、文化認同感的基礎之上的,村上春樹也是如此。早年的村上春樹對美國文學抱有極大的幻想,對自己本國的文化認同感并不強。但是,隨著創(chuàng)作的不斷深入,創(chuàng)作時間的不斷延長,村上春樹漸漸發(fā)現(xiàn):一個人人格的完整,與兩樣東西密不可分,一是土地,二是家園。所以,對于傳統(tǒng)文學的重視和研習就成了他必修的功課。
一部文學作品、一位作家的成功,與其所處的文化環(huán)境、文學傳統(tǒng)有關,但最核心的因素,必然是其強大的思想性、獨特的藝術性,村上春樹的作品即是如此。村上春樹的小說有著強烈的人文色彩和獨特的個性,無論是人物刻畫,還是創(chuàng)作風格,都打破了人們對傳統(tǒng)日本文學的印象。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歐洲的浪漫主義精神與“存在主義”立場,也看到了美國式的“個人救贖”,可以說,村上作品的復雜度遠遠超過了當下日本的任何一位作家,幾乎達到了這個時代“自我意識書寫”的巔峰。
《挪威的森林》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將日本文學中最可貴的現(xiàn)實主義筆法,與上世紀美國小說的突出風格相結合,就此打通了一條專屬于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之路。村上春樹在隨后的作品中,也都生動地反映了現(xiàn)代人心靈的動蕩、無助、焦慮與救贖的渴望,并且提出了許多發(fā)人深省的文化命題,例如如何讓一個人擺脫精神性的孤獨、如何體會生與死的痛苦。這些命題無一例外地將筆觸伸向現(xiàn)實的“人”以及人的生存,而不再是空泛的“無病呻吟”。
在《海邊的卡夫卡》中,我們也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那就是民族文化中一些本質(zhì)的、生存層面的東西,總是在他的作品中不經(jīng)意地流露了出來。可以說,《海邊的卡夫卡》中出現(xiàn)的大量日本文學的信息,意味著美國文學已不再是村上小說創(chuàng)作的唯一源頭。村上春樹說過,“寫完《奇鳥行狀錄》以后,不知為什么,日甚一日地、特別想‘應該趕緊回到日本’。既沒有什么特別思念的東西,也不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回歸,只是覺得作為小說家,我應該待的地方還是日本”。
二、村上春樹小說人物的獨特個性
1、人格塑造的過度性、荒誕性
論及村上春樹小說的創(chuàng)作個性,還得從《挪威的森林》入手。這部小說問世之初,飽受爭議的焦點不是故事,而是人物。小說中女主角的過度犧牲,以及因男主角而遭受的百般痛苦,均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圍。這種過度的、過分放大的人物形態(tài),似乎更應該出現(xiàn)在話劇舞臺上、電影屏幕上,而不是言情小說里。
在小說《且聽風吟》里,村上春樹則用“過度性”的筆法勾勒出一個人性扭曲、價值顛覆的小世界。在一個混亂的城市,“我”遇到了一個同樣來歷不明的醉酒女子,一番稀里糊涂的接觸之后,兩個人開始互訴衷腸。在城市的夜晚,女人們習慣用酒精麻痹自己,使自己暴露在男人的視線之中,可是醒來后,卻對關懷自己的人又是提防、又是懷疑。這樣的人和事,一般人是很難接受的,可是身為主人公的“我”全然不介意,也沒覺得有什么不妥。假期結束之后,“我”回城,故事也就這樣結束。
村上小說還有一個普遍的特質(zhì):孤獨與自由。這兩者在本質(zhì)上并不矛盾。在關于浪漫主義文學的研究當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種觀點,即“自由是浪漫主義者在感受個體孤獨之后,情感上最深切的抒發(fā)”。村上的小說著力反映的,其實是深陷物欲之中的年輕人的世界,對于潛藏于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虛無主義和頹廢情緒的挖掘,可謂是下足了工夫。因為現(xiàn)實太苦悶,所以村上春樹才要努力在作品中凸顯一種反秩序、反權威、反體制的精神動向,只有這樣,孤獨在與自由的“角力”中才不會敗下陣來,現(xiàn)實的人生也才有了繼續(xù)向前的可能。
一些村上小說的研究者認為,就《挪威的森林》、《且聽風吟》這樣的作品而言,在敘述方式、作品風格上,都具有實驗性、超前性。可事實上,這些小說并沒有太多刻意為之的痕跡,表現(xiàn)手法上也并不強烈,它們只是以藝術化的手法夸大了一切“痛”與“欲”所帶來的悲歡。這也是村上春樹所希望達到的,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消除人內(nèi)心的種種困擾,就像主人公直子所希望的,從根本上“救贖”自己、解放自己。
2、女性意識的強烈凸顯
小說《挪威的森林》,被認為是六七十年代女性意識覺醒的在文學上的一種反映。這種覺醒有兩層含義:一是愛情上的覺醒;一是生存方式上的覺醒。
小說精心刻畫了直子、綠子、玲子和初美等幾位頗具個性的女性。高中階段的直子,因為男友木月的自殺而憂郁成疾,為了擺脫自己內(nèi)心的魔障,住進了療養(yǎng)院。直子用自己的壓抑,回應了與渡邊的愛情,也希望借此懷念死去的木月。村上春樹在這里給讀者留下了一個疑團,那就是:直子與渡邊之間是否存在真愛?即便是直子的死,也無法表明她最終越過木月而接受渡邊。可見,作品仍然保留了對現(xiàn)實愛情的美好期許,村上并不愿赤裸裸地撕裂一段復雜而動人的三角戀情。這樣,一個跳出作品之外的、悲觀而銷魂的女性形象便躍然紙上。
村上春樹1988年發(fā)表的長篇小說《舞舞舞》,也凸顯了強烈的女性立場。“被上帝拋棄的寵兒”雪,自幼就過著悲天憫人的生活。忠于愛情的美麗女子“喜喜”,則被當紅影星五反田無辜刺死。如果說五反田是在他者的視野中迷失了自我,那么被殺害的“喜喜”則是女性意識覺醒前的最后一個冤魂。
村上的小說往往以自我為中心,小說的主人公也大都是一副玩世不恭、我行我素的姿態(tài),幾乎對政治漠不關心。此外,村上早期的作品重抒情、輕情節(jié),有些片段故事性并不強,但語言的趣味性和天馬行空一般的想象力,還是讓崇尚享樂的青少年們感到滿意。年輕的讀者們,根本不想探求文學本身的深刻意義,而只愿停留在對具有原創(chuàng)性、想象力事物的好奇和追逐的層面上,而村上小說正好契合了他們的這一訴求,帶給他們以審美體驗和閱讀上的快感,讓他們找到了“最真的自己”,還原了“最真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