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5-09-06所屬分類:經(jīng)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如何加強對票據(jù)管理應用的新技巧呢?什么樣的票據(jù)應用是現(xiàn)在發(fā)展的一個趨勢呢?又該如何去加強對金融管理的應用呢?本文主要從關于票據(jù)代理、票據(jù)簽名和票據(jù)金額記載問題的修改建議和關于票據(jù)法律關系、票據(jù)抗辯制度以及票據(jù)權利等的修改建議以及票據(jù)變造的責任
如何加強對票據(jù)管理應用的新技巧呢?什么樣的票據(jù)應用是現(xiàn)在發(fā)展的一個趨勢呢?又該如何去加強對金融管理的應用呢?本文主要從關于票據(jù)代理、票據(jù)簽名和票據(jù)金額記載問題的修改建議和關于票據(jù)法律關系、票據(jù)抗辯制度以及票據(jù)權利等的修改建議以及票據(jù)變造的責任認定等各個方面做了介紹。本文選自:《新金融》,《新金融》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正式批準公開發(fā)行的優(yōu)秀期刊。自創(chuàng)刊以來,以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為主題,堅持"期期精彩、篇篇可讀"的理念。新金融內(nèi)容詳實、觀點新穎、文章可讀性強、信息量大,眾多的欄目設置,新金融公認譽為具有業(yè)內(nèi)影響力的雜志之一。新金融并獲中國優(yōu)秀期刊獎,現(xiàn)中國期刊網(wǎng)數(shù)據(jù)庫全文收錄期刊。
摘要:我國《票據(jù)法》第8條規(guī)定,票據(jù)金額以中文大寫和數(shù)碼同時記載,二者必須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據(jù)無效。可是,借鑒國外的一般做法,即便票據(jù)金額記載出現(xiàn)二者不一致的情況,為了維護票據(jù)交易的安全,在法解釋學上也應該朝著盡量使已發(fā)生的行為有效的方向進行解釋。我國《票據(jù)法》的該條規(guī)定顯然過于嚴苛,與會學者就此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和理由。
關鍵詞:票據(jù),經(jīng)濟管理,金融論文
Our abstract: instrument law stipulated in article 8, the sum in Chinese capital and digital records at the same time, both must agree, both is inconsistent, paper is invalid. , however, the common practice of draw lessons from abroad, even if the bill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amount recorded in both cas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paper deals, in hermeneutics should also be on towards the behavior of effective make have been explained. The regulation in our country, which apparently is too harsh, the scholar to put forward the concrete revision opinion and reasons.
Keywords: paper, economic management, the financial papers
一、關于票據(jù)代理、票據(jù)簽名和票據(jù)金額記載問題的修改建議
(一)越權代理時票據(jù)責任分別承擔會影響票據(jù)權利不可分原則
票據(jù)作為一種有價證券,持票人以其持有的票據(jù)證明其權利,在到期日之前提示票據(jù)請求對方付款來實現(xiàn)自己的權利,付款結束后,持票人還應將票據(jù)繳回履行付款義務的債務人。我國《票據(jù)法》第5條第2款規(guī)定:“代理人超越代理權限的,應當就其超越權限的部分承擔票據(jù)責任。”按其意旨,當發(fā)生越權代理的時候,持票人以一張票據(jù)分別向被代理人和無權代理人請求付款,這明顯違反了票據(jù)的不可分性原則。票據(jù)是典型的有價證券,既為有價證券就需要維持其完整性、不可分性。所以,該條規(guī)定在實務上不具有可操作性。《票據(jù)法》施行以來就有不少學者對該條款提出了批評。[1]
然而,圍繞我國《票據(jù)法》第5條第2款規(guī)定的內(nèi)容是否違反了票據(jù)不可分原則,與會學者因觀點各異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吉林大學法學院趙新華教授在發(fā)言中給出了解決該問題的方案,即將本條修改為“代理人超越代理權限的,代理人得就其超越權限的部分承擔票據(jù)責任,但不妨礙票據(jù)權利人向代理人要求由其承擔全部票據(jù)責任”。西南政法大學的汪世虎教授也認為,《票據(jù)法》第5條第2款關于越權代理的規(guī)定破壞了票據(jù)金額的不可分性原則,實務中也難以操作,因此宜采“全額責任說”,即越權代理人與無權代理人負同一責任。還有學者認為,從票據(jù)權利的單一性考慮,不應允許持票人就一項票據(jù)權利分別向兩人行使,而從票據(jù)的完全有價證券性質(zhì)的角度也可以解釋這一規(guī)定是錯誤的。
與此相反,上海政法學院的湯玉樞教授則認為,從我國現(xiàn)行《票據(jù)法》整體來看,其維持了票據(jù)金額的不可分性,唯獨在越權代理的情況下,其認可票據(jù)金額是可以分開的;票據(jù)金額是否可分在技術上不存在問題,故票據(jù)金額是可分的,認定票據(jù)金額可分的好處是可以增強票據(jù)的信用,促進票據(jù)流通,保證票據(jù)交易安全,如果票據(jù)金額不可分就會與《票據(jù)法》第5條第2款的規(guī)定發(fā)生矛盾,以致陷人兩難的境地。持與此相近立場的中國工商大學的呂來明教授指出:“票據(jù)金額的不可分性本身就是相對的,各國也有不同規(guī)定。在操作上,發(fā)生越權代理時,被代理人與代理人各自承擔相應的票據(jù)責任,支付相應的金額,具有其正當性。另外,在我國的實踐中票據(jù)代理很少出現(xiàn),現(xiàn)有規(guī)定未能在實踐中反映出存在明顯缺陷,故無需修改該條款。票據(jù)金額的可分性與否,還應該與是電子票據(jù)還是紙質(zhì)票據(jù)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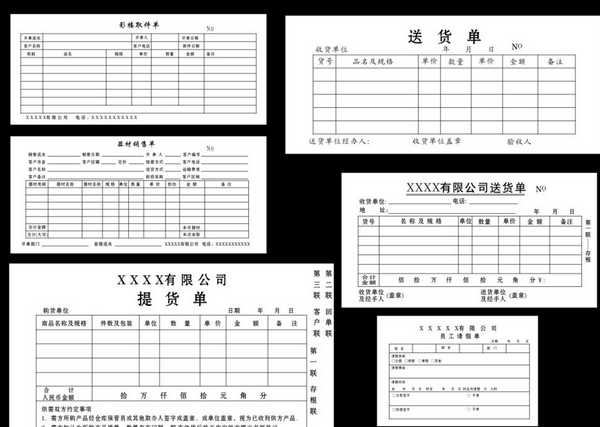
認為我國《票據(jù)法》第5條第2款規(guī)定違反票據(jù)金額可分性和有價證券完整性的學者,提出了無權代理人全額責任說。該觀點的本意在于,就越權代理人來說,相對于票據(jù)權利人其必須承擔全部票據(jù)責任,而相對于被代理人則只承擔越權部分的票據(jù)責任;在越權代理人已經(jīng)向票據(jù)權利人承擔了全部票據(jù)責任時,可向被代理人主張本應由其承擔的原代理權限內(nèi)的那一部分票據(jù)責任,從而避免了就一張票據(jù)向兩個人分別付款的問題,維護了票據(jù)的完整性與不可分性。[2]當然,目前電子化票據(jù)的快速發(fā)展使得票據(jù)金額不可分的固有原則遭受到嚴重的挑戰(zhàn)。在這樣的背景下,本著從實際出發(fā)的原則,廈門大學法學院的劉永光副教授提出了一個靈活的方案。其認為,首先要區(qū)分紙質(zhì)票據(jù)和電子票據(jù),紙質(zhì)票據(jù)的金額是不可分的,而電子票據(jù)的金額是可分的。2008年頒布的《日本電子債權記錄法》即規(guī)定電子票據(jù)的金額是可分的,該立法例可供借鑒。 由中國法學會商法研究會主辦、華東政法大學經(jīng)濟法律研究院承辦的第一次全國票據(jù)法修改研討會于2010年10月9日在上海舉行,中國法學會商法研究會王保樹會長,中國法學會商法研究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顧功耘,我國臺灣地區(qū)施文森大法官,中國人民銀行條法司王玉玲副司長與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最高人民檢察院民行廳、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服務部分別派代表出席會議。與會的票據(jù)法學者以及法官、律師等30余人就我國現(xiàn)行《票據(jù)法》中存在的問題展開了積極的討論。本次會議圍繞三大議題展開,即票據(jù)法總則部分的票據(jù)代理理論、票據(jù)金額記載,票據(jù)無因性、票據(jù)善意取得、利益返還請求權,以及票據(jù)變造。議題多、涉及面廣、理論聯(lián)系實踐性強是此次會議的特點,現(xiàn)將會議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票據(jù)無權代理的追認問題也是學界長期以來討論的話題,本次會議的與會學者一致認為票據(jù)無權代理可以追認。雖然我國《民法通則》第66條規(guī)定了無權代理行為可以追認,但我國《票據(jù)法》并沒有這方面的規(guī)定。圍繞將來修改的《票據(jù)法》是否應增加此項規(guī)定的問題,與會學者發(fā)表了不同見解。黑龍江大學的董惠江教授認為,關于無權代理追認,從票據(jù)法和民法的關系考慮,票據(jù)法未作規(guī)定的,當然應適用民法的規(guī)定。另外,票據(jù)代理制度是私法制度,應體現(xiàn)意思自治原則,當發(fā)生無權代理時,本人愿意追認的,應該對當事人這一自由意思的表達予以尊重。此外,票據(jù)關系中的被代理人一般是處于經(jīng)濟上的強勢,而代理人則處于弱勢,允許被代理人追認能增強票據(jù)的清償能力,從而保護票據(jù)交易安全,其符合票據(jù)流通的基本理念。至于是否在《票據(jù)法》中增加相應的條款規(guī)定這一問題,《票據(jù)法》還是以不作明確規(guī)定為宜,在發(fā)生無權代理本人追認的場合,完全可適用民法關于代理的規(guī)定。
但也有與會學者提出,在《票據(jù)法》第5條第2款原有條文上增加有關票據(jù)無權代理行為可以追認的規(guī)定則更為明確。汪世虎教授認為,可以在《票據(jù)法》第5條第2款“應當由簽章人承擔票據(jù)責任”后明確增加一項除外規(guī)定,即“被代理人追認的除外”。對此,華東政法大學的楊忠孝教授則認為,追認是意思表示的表達問題,由于追認有對物的效力和對人的效力這兩種情形,如果要考慮追認的話,一定要考慮如何讓追認的意思在票據(jù)上表達出來,所以要在立法技術上解決這個問題。
(二)關于票據(jù)簽名問題
我國《票據(jù)法》第7條第3款規(guī)定:“票據(jù)上的簽名,應當為該當事人的本名。”這一規(guī)定因過于剛性而備受學者批評。姓名或名稱記載的目的在于讓票據(jù)取得人能夠辨明票據(jù)行為人與票據(jù)記載的姓名或名稱是否具有一致性和同一性,以便于其在票據(jù)期限屆滿時,能夠通過票據(jù)上記載的姓名和名稱準確確定票據(jù)債務人并向其請求付款。不少學者提出,債務人名稱的記載,只要足以判明其為“同一性”,即不論以何種方式記載付款人名稱,只要能夠判明其為誰人即可。我國《票據(jù)法》對票據(jù)簽名的嚴格限制條款已不合時宜,應當放開對簽名的限制。在如今彰顯個性的時代,使用筆名、藝名的現(xiàn)象十分普遍,而且不少筆名和藝名在社會上的知曉度甚至超過了本名,此時使用筆名、藝名或許更易于為相對方所接受。將姓名記載于票據(jù)上的目的僅是為了使票據(jù)權利人能夠確定債務人和使其承擔責任,票據(jù)當事人簽署的筆名、藝名等并不妨礙這個目的的實現(xiàn),因此沒有必要嚴格規(guī)定票據(jù)上的簽名只能為當事人的本名。[3]
對于《票據(jù)法》第7條第3款的規(guī)定,與會專家提出了具體的肯定或否定的意見。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的柯昌輝老師認為,簽名只是為了確認票據(jù)權利和票據(jù)權利主體的合一性。雖然實名制對于銀行系統(tǒng)的反洗錢活動非常有益,從金融管制的角度來看其是可行的,但《票據(jù)法》有關簽名的規(guī)定只是用于確定私權的歸屬,將實名制推行至票據(jù)法領域是不合適的。因此,金融監(jiān)管的理念和私法的理念是有很大不同的,或者說是各有各的分工,不應彼此混淆,票據(jù)上的簽名不應該僅限于當事人的本名。寧波大學鄭孟狀教授持相同立場,認為我國《票據(jù)法》的主要問題是票據(jù)的使用推廣不夠廣泛,票據(jù)的流通性沒有得到充分體現(xiàn),此外,相關法律法規(guī)、判例之間也存在相互沖突,《票據(jù)法》、中國人民銀行《票據(jù)管理實施辦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jù)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之間不一致的地方有很多。其認為,從票據(jù)流通的角度來說,應該賦予持票人選擇權,票據(jù)簽名也是這樣,簽名應可以是筆名、藝名等任何名字,只要表明社會認知即可;只要筆名、藝名等能夠“足以表明當事人身份”,其事實上就代表了一種社會的認知;我國《票據(jù)法》對票據(jù)簽名的限制過于嚴格,這有違主體平等性的原則。另有學者認為,對于票據(jù)當事人應使用本名進行簽名的規(guī)定應該從寬適用,因為在我國未來的簽名方式會比較多,從這一點上來說,只要可以確定簽名人的身份,足以識別簽名人即可。
然而堅持“票據(jù)簽名以本名為原則”立場的學者也不在少數(shù)。華東政法大學的陳岱松副教授認為:“票據(jù)上簽名還應使用本名而非藝名。簽名對于票據(jù)來說是一件很嚴肅的事。另外還有一個對于簽名的效力問題。在國外,簽名的效力高于印章。相比印章,簽名更加難以模仿。所以個人認為,簽名應該是簽本名,但是藝術性簽名也是簽名,何種字體都是可以的,重要的是足以表明其身份。”贊成這一觀點的山東大學董翠香副教授認為,如果票據(jù)簽名可為藝名,則該藝名的社會認知度一定要很高,否則票據(jù)經(jīng)多次轉(zhuǎn)讓后,后手無法識別該藝名使用者的身份,因而不敢貿(mào)然受讓該票據(jù),其結果必然不利于票據(jù)的流轉(zhuǎn);而如果要求當事人使用的藝名具有較高的社會認知度也不切合實際,因為滿足這一條件的人畢竟是非常有限的,為這一有限范圍的人特別制定規(guī)則是對立法資源的浪費。華東政法大學的曾大鵬博士也認為,就票據(jù)簽章而言,要么是自然人,要么是法人。身份證是銀行用以識別自然人身份的基本途徑,因此使用身份證上載明的姓名是票據(jù)簽名的最佳選擇,采用藝名、別名等易導致未來“過河拆橋”等背信情況的出現(xiàn)。
(三)關于票據(jù)金額記載問題
呂來明教授的修改意見是,出票人記載的票據(jù)金額應以中文大寫和數(shù)碼同時記載,二者不一致的,以中文大寫為準;《票據(jù)法》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因為多數(shù)國家、地區(qū)和相關國際公約均規(guī)定匯票金額的文字記載與數(shù)碼記載不一致時,以文字記載為準,數(shù)次記載不符的以較小數(shù)額為準。這在出票人因筆誤出現(xiàn)錯寫時對于確定其票據(jù)效力和維護持票人利益是必要的。日本獨協(xié)大學周劍龍教授在從中日票據(jù)法律制度對比的視角進行分析后指出,我國國內(nèi)目前對《票據(jù)法》第8條規(guī)定進行修改的主流意見是,票據(jù)金額的中文大寫與數(shù)碼二者不一致的,以金額中文大寫為主。在這方面日本有兩個處理原則,一個是文字優(yōu)先,另一個是最小金額優(yōu)先。從法律角度來說,當票據(jù)金額的中文大寫和數(shù)碼二者不一致時,應以金額最小為優(yōu)先原則并將其納入我國修訂后的《票據(jù)法》中。
二、關于票據(jù)法律關系、票據(jù)抗辯制度以及票據(jù)權利等的修改建議
(一)關于票據(jù)無因性問題
我國《票據(jù)法》第10條第1款規(guī)定:“票據(jù)的簽發(fā)、取得和轉(zhuǎn)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該規(guī)定在《票據(jù)法》頒布后即備受爭議,并受到諸多批評。此處所規(guī)定的“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是否應視為票據(jù)行為成立的有效要件?該規(guī)定是否破壞了票據(jù)的無因性?
對此問題呂來明教授指出,現(xiàn)行《票據(jù)法》第10條第1款規(guī)定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否定票據(jù)的無因性,而是限定沒有支付對價的融通票據(jù)在市場上流通。從實踐意義上講,這一規(guī)定并非是對于票據(jù)無因性原則取舍做出選擇,而是基于我國金融政策的需要對融通票據(jù)作出的適度限制。從經(jīng)濟和金融發(fā)展的現(xiàn)實出發(fā),在未來一段時期和特定領域內(nèi),堅持票據(jù)的簽發(fā)、取得和轉(zhuǎn)讓須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這一要求對于票據(jù)市場乃至金融市場的健康發(fā)展是十分必要的。鄭孟狀教授認為,票據(jù)的簽發(fā)和轉(zhuǎn)讓當然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該規(guī)定僅僅是限制票據(jù)的融資,其作為一個宣示性條款絕不會破壞票據(jù)的無因性原則,而且自《票據(jù)法》實施以來,無論是在銀行交易業(yè)務中還是在商業(yè)實踐中從來沒有人否定票據(jù)的無因性,最高人民法院也一直堅持票據(jù)無因性。同時,其認為《票據(jù)法》第10條第1款的文字表述可以再予斟酌,建議刪除“真實的交易關系”這一表述。
持相反意見的董惠江教授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jù)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明確規(guī)定不能將《票據(jù)法》第10條作為抗辯條款予以適用,但仍有基層法院的法官將《票據(jù)法》第10條第1款當作票據(jù)有效性的條款加以引用。因此,《票據(jù)法》存在這樣的條款會招致許多麻煩,建議予以刪除。
華東政法大學李偉群教授認為,其實在1995年《票據(jù)法》頒布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就“中國農(nóng)業(yè)銀行西寧市支行東郊辦事處訴中銀信托投資公司銀行承兌匯票糾紛上訴案”、“交通銀行中山支行訴中國成套設備出口公司武漢分公司經(jīng)營處、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海口市分行等銀行承兌匯票糾紛再審案”作出的重要判例就已表明其堅持票據(jù)無因性立場。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4日頒布的《關于審理票據(jù)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14條規(guī)定:“票據(jù)債務人不得以《票據(jù)法》第10條、第21條的規(guī)定為由,對業(yè)經(jīng)背書轉(zhuǎn)讓票據(jù)的持票人進行抗辯。”其再一次強調(diào)了堅持票據(jù)無因性的立場。我國《票據(jù)法》采用了票據(jù)無因性原則,其依據(jù)為第4條有關票據(jù)文義性(票據(jù)權利內(nèi)容以票據(jù)上記載文字為準)的規(guī)定和第22條第2款有關票據(jù)單純性(票據(jù)到期后無條件付款)的規(guī)定。然而《票據(jù)法》第10條第1款究竟是效力性規(guī)定還是宣示性條款,學界的相關解釋均有其合理之處。從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貫立場來看,《票據(jù)法》第10條第1款規(guī)定應該解讀為宣示性條款。但是,由于目前在我國票據(jù)知識還很不普及,要讓普通民眾將該條款內(nèi)容理解為宣示性條款尚有一定難度,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混亂。鑒于此,建議對該條款內(nèi)容作進一步修改或者索性將之取消,而將這一宣示性條款納人中國人民銀行制定的《票據(jù)管理實施辦法》中比較合適。
(二)票據(jù)善意取得制度和人的抗辯限制制度是促進票據(jù)流通的兩大支柱
我國現(xiàn)行《票據(jù)法》第12條、第13條分別規(guī)定了票據(jù)善意取得制度和人的抗辯限制制度。關于票據(jù)權利的善意取得制度,《日內(nèi)瓦統(tǒng)一票據(jù)法》以及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票據(jù)法都有類似的規(guī)定,即“匯票占有人依背書的連續(xù)證明其權利時,視為合法的持票人。不問因何事由,有喪失匯票占有者時,持票人如能依前項規(guī)定證明其權利,則不負返還義務。但是,持票人因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匯票時,不在此限”。解讀該條文可知,持票人以票據(jù)背書連續(xù)即可證明其為正當?shù)钠睋?jù)權利人,其取得票據(jù)無需返還原票據(jù)權利人(失票人)。但是,持票人因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匯票者除外。
與此相對,我國《票據(jù)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結構與上述各大陸法系國家的結構正好相反,把他們條文中的“但書”規(guī)定的內(nèi)容放在了我們的主文中。我國《票據(jù)法》第12條規(guī)定,出于惡意取得票據(jù)的,不得享有票據(jù)權利;持票人因重大過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規(guī)定的票據(jù)的,也不得享有票據(jù)權利。該條款未正面規(guī)定票據(jù)善意取得制度,而是需要從反面解釋其意旨,即只有受讓人無惡意或沒有重大過失地從無權利人手中獲得票據(jù)的,其票據(jù)權利才受到保護。針對我國《票據(jù)法》第12條的內(nèi)容和構成,與會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批評意見。曾大鵬博士認為,我國票據(jù)法上的善意取得是從反面來說的,即善意或者無重大過失取得票據(jù)者受到保護,這個規(guī)定不如《物權法》從正面規(guī)定善意取得制度直接。關于遺失票據(jù)的取得問題,在物權法上已有規(guī)定,遺失物不存在善意取得的問題。但在票據(jù)法上,按照英美法相關立法以及《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相關規(guī)定,遺失的票據(jù)可以適用善意取得。因此,遺失票據(jù)的取得應當與民法上的遺失不可成立善意取得有所區(qū)別。
關于我國《票據(jù)法》第12條第1款的規(guī)定,趙新華教授認為,“以詐欺、脅迫”手段取得票據(jù)屬于一般民事規(guī)定,與偷盜獲得票據(jù)是完全兩碼事,并且欺詐、脅迫是民法上的意思表示問題,也不應該與偷盜置于同一條款中。因為此三種情形并非同一性質(zhì),放在同一條文中很難理解,建議將“以欺詐、脅迫”手段取得票據(jù)內(nèi)容刪除。對此周劍龍教授也認為,偷盜與欺詐、脅迫完全是兩回事。欺詐、脅迫是意思表示方面內(nèi)容,應交由民法進行討論。《日本票據(jù)法》第16條第2款是關于善意取得的內(nèi)容。該條款規(guī)定:“不問因何事由,有喪失匯票占有者時,持票人如能依前項規(guī)定證明其權利,則不負返還義務。”該條款中根本沒有欺詐、脅迫方面的內(nèi)容。對于我國《票據(jù)法》第12條第2款“持票人因重大過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規(guī)定的票據(jù)的,也不得享有票據(jù)權利”之內(nèi)容,柯昌輝老師認為,其中的“不符合本法規(guī)定”所指內(nèi)容不明,如此規(guī)定實屬過于寬泛,建議票據(jù)法修改時,對善意受讓作出正面規(guī)定。
與會學者就我國《票據(jù)法》第13條關于人的抗辯限制的規(guī)定圍繞如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該條第1款規(guī)定的惡意抗辯的成立要件應如何予以認定?該條第1款的內(nèi)容是否完善?該條第2款規(guī)定直接當事人之間可以抗辯以及第3款規(guī)定抗辯的定義有無必要?
對此,吉林大學法學院的王艷梅副教授認為,《票據(jù)法》第13條第1款僅僅指的是債務人不能援用前手對人抗辯的限制,該條文表述不盡周延;《票據(jù)法》第13條第2款其實就是適用第1款規(guī)定進行逆推的結果,雖然《日內(nèi)瓦統(tǒng)一票據(jù)法》及我國臺灣地區(qū)“票據(jù)法”上均無此規(guī)定,但是考慮到法律適用的方便及邏輯的完整性,建議保留此條文;至于《票據(jù)法》第13條第3款則無必要,可以刪除。此外,在日本有“權利濫用抗辯”一說,即債務人不能沿用后手對持票人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但是在持票人與其前手之間的原因關系無效或者被解除之場合,其不將票據(jù)返還前手反倒向債務人請求付款的,債務人則可以權利濫用為由進行抗辯。但日本“權利濫用抗辯”未規(guī)定于票據(jù)法中。不過,從立法技術和法律內(nèi)容的完整性角度考慮,我國《票據(jù)法》第13條可以納人該抗辯內(nèi)容。
柯昌輝老師則認為,《票據(jù)法》第13條第2款是有關抗辯原因的規(guī)定,從實際生活的情形看,此類抗辯原因有很多,《票據(jù)法》難以用列舉的方式一一窮盡,最好的辦法是由司法解釋來解決,故建議刪除該款規(guī)定;由于票據(jù)法存有完全不同于民法的法理依據(jù),加之票據(jù)法的專用術語非常多,票據(jù)使用人和法官可能會以民法原理來理解票據(jù)法問題,建議像英美法那樣設置一個條款來集中規(guī)定票據(jù)法專用術語的解釋。華東政法大學的傅鼎生教授從票據(jù)法與民法上抗辯權的銜接角度指出,應刪除《票據(jù)法》第13條第2款。該款規(guī)定給人的錯覺是只有不履行合同義務的才發(fā)生直接抗辯,其解決方案有二:一是刪除該款,二是將其修改為“票據(jù)債務人可基于基礎關系中的抗辯事由對抗與自己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的持票人”。
對于《票據(jù)法》第13條的上述三款內(nèi)容,李偉群教授從另一角度提出了修改建議:《票據(jù)法》第13條第1款的但書明確規(guī)定,明知有抗辯事由存在而受讓票據(jù)的構成惡意。問題是,受讓人取得票據(jù)時明知抗辯事由存在而有惡意,可是在票據(jù)到期日之前出現(xiàn)了類似債務相互抵消或者約定的義務已經(jīng)履行等抗辯事由消失的情形,致使惡意不復存在,再定其為惡意抗辯顯然變得離譜。所以該條第1款的規(guī)定范圍過于寬泛,難免會有疏漏,建議不應將惡意抗辯成立與否的認定時間放在受讓人取得票據(jù)的一個時點上,而是應將其放在從受讓人受讓票據(jù)時起至票據(jù)到期日為止的這一時段中;至于同條第2款的存在已無必要—既然第1款規(guī)定債務人不得以與自己有直接債權債務關系當事人的抗辯事由對抗第三人,那么反之,債務人當然可以對與自己有直接關系的持票人進行抗辯。因此該款規(guī)定可以刪除;同條第3款是何為票據(jù)抗辯的解釋,將這樣的內(nèi)容列人條文實無必要,建議刪除。
(三)票據(jù)權利是一種在交易過程中形成的債權
票據(jù)作為一種流通證券,票據(jù)行為人對其都有嚴格的票據(jù)義務,權利的消滅時效越長則票據(jù)債務人的義務風險越不能確定,從而增加了債務人的負擔。為此,對于權利人可以并能夠行使權利而不行使的,法律規(guī)定其票據(jù)權利將喪失。我國《票據(jù)法》第17條規(guī)定票據(jù)權利在下列規(guī)定的期限內(nèi)不行使而消滅:(1)持票人對票據(jù)的出票人和承兌人的權利,自票據(jù)到期日起2年。見票即付的匯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2)持票人對支票出票人的權利,自出票日起6個月。(3)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6個月。(4)持票人對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3個月。對于《票據(jù)法》第17條規(guī)定的短期的消滅時效的統(tǒng)一性和合理性也受到熱議。王艷梅副教授指出,《票據(jù)法》第17條第1款第1項規(guī)定,持票人對出票人、承兌人的權利自票據(jù)到期日起2年內(nèi)不行使而消滅。持票人對見票即付的匯票、本票的權利自出票日起2年內(nèi)不行使而消滅。建議對見票即付的匯票、本票的消滅時效改為從見票日起2年,這樣能夠讓持票人行使票據(jù)權利的期限延長一些,更有利于持票人權利的保護。
煙臺大學于永芹教授認為,我國《票據(jù)法》第17條關于追索權時效起算日的規(guī)定欠妥。首先,該條第I款第3項規(guī)定持票人對前手的追索權為“自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之日起6個月”。這樣的規(guī)定并不能完全滿足實踐的需要。因為持票人行使追索權的原因不限于被拒絕承兌和被拒絕付款,還包括承兌人或付款人死亡、逃匿、被依法宣告破產(chǎn)或因違法被責令終止業(yè)務活動等情形。一般說來,持票人只有在票據(jù)到期提示付款時,才能了解付款人死亡、逃匿、被宣告破產(chǎn)、被責令終止業(yè)務活動等情況,所以消滅時效的起算日不能單純考慮被拒絕承兌或者被拒絕付款的場合,還應該覆蓋這些情況,合理設定追索權的時間。其次,該條第1款第4項規(guī)定“持票人對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3個月”。這里的“被提起訴訟日”,是指持票人向再追索權人提起訴訟的日期。通常,持票人向再追索權人提起訴訟需要較長的時間,如果該案件除了經(jīng)過一審、甚至還有二審乃至再審程序的話,整個訴訟程序的時間早就超過了3個月的消滅時效。因此該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算方法明顯不妥,建議修改為“訴訟案件終結生效之日”起開始計算其對前手行使再追索權的時效期間。
此外,董惠江教授認為,《票據(jù)法》第17條第1款第4項“持票人對前手的再追索權,自清償日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3個月”之表述中的“或者被提起訴訟之日起”應予刪除。其理由是:訴訟時效或消滅時效都是針對權利人可以并能夠行使權利而不行使權利的狀態(tài)。雖然票據(jù)債務人被提起訴訟,但在法院的調(diào)解書或判決書生效之前都不能說票據(jù)債務人一定要承擔這一償還義務,因為票據(jù)債務人提出的抗辯完全可能使其自己勝訴。而在沒有履行償還義務之前,債務人無法收回票據(jù)及其他相關證明向前手展開再追索,也就是票據(jù)債務人的再追索權尚未產(chǎn)生,而按上述規(guī)定其時效就已開始計算了,這從根本上違背了時效制度的原理。另外,依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guī)定,一審普通程序的審理期限是6個月(有特殊情況的還可延長),如果3個月內(nèi)案件沒有審結,被起訴的票據(jù)債務人就要選擇主動履行以保全再追索權,或者承擔3個月后敗訴并喪失對前手的再追索權的風險,這顯然造成了票據(jù)法與訴訟法的不協(xié)調(diào)。
(四)關于利益返還請求權的發(fā)生原因
我國《票據(jù)法》第18條規(guī)定:“持票人因超過票據(jù)權利時效或者因票據(jù)記載事項欠缺而喪失票據(jù)權利的,仍享有民事權利,可以請求出票人或者承兌人返還其與未支付的票據(jù)金額相當?shù)睦妗?rdquo;可是在“票據(jù)記載事項欠缺”的場合,票據(jù)效力也無從產(chǎn)生。因此,該條規(guī)定顯然是票據(jù)立法上的失誤和疏漏。對此,于永芹教授指出,在我國目前的票據(jù)實務中,票據(jù)欠缺絕對應記載事項的情況時有發(fā)生,由于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票據(jù)法》對于票據(jù)的嚴格形式要求,欠缺絕對應記載事項的票據(jù)被當作有效票據(jù)進行使用和多次流轉(zhuǎn)的現(xiàn)象絕非罕見,此時的持票人確已不能享有票據(jù)權利,但持票人取得該無效票據(jù)是支付了一定對價的,沒有票據(jù)權利就意味著損失的發(fā)生;從制度設計和有機銜接的角度考慮,《票據(jù)法》應當設立相應的制度,對這樣的無效票據(jù)引起的法律關系予以調(diào)整,而不能僅僅規(guī)定其無效了之,這也是票據(jù)法促進票據(jù)快速流轉(zhuǎn)和確保票據(jù)交易安全這一立法宗旨的要求。為此,其建議將《票據(jù)法》第18條修改為:“持票人因超過票據(jù)權利時效期間或者票據(jù)保全手續(xù)欠缺而喪失票據(jù)權利,或因票據(jù)絕對應記載事項欠缺而導致票據(jù)無效的,可以請求實際受益人返還與其實際受益相當?shù)睦妗?rdquo;
對此提出相反意見的湯玉樞教授認為,對于欠缺記載事項的票據(jù)而言,其票據(jù)權利原來就不存在,不管它經(jīng)過多少次善意的流轉(zhuǎn)都不可能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權利。票據(jù)為設權證券,這個權利是由出票人創(chuàng)設的,在出票人簽發(fā)票據(jù)時因記載事項欠缺而導致票據(jù)無效的情況下,這張票據(jù)上不可能存在票據(jù)權利。所以,其認為一張因記載事項欠缺而無效的票據(jù)不管經(jīng)過多少次流轉(zhuǎn),其上都不應當存在票據(jù)權利,建議將《票據(jù)法》第18條中的“記載事項欠缺”改為“必要保全手續(xù)欠缺”。
三、票據(jù)變造的責任認定
關于票據(jù)變造的責任認定問題,也是這次研討會的主要議題之一。《票據(jù)法》第14條第3款規(guī)定:“票據(jù)上其他記載事項被變造的,在變造之前簽章的人,對原記載事項負責;在變造之后簽章的人,對變造之后的記載事項負責;不能辨別是在票據(jù)被變造之前或者之后簽章的,視同在變造之前簽章。”對于票據(jù)變造問題,由于票據(jù)文義發(fā)生了變化,權利義務關系也發(fā)生了變化,因而在票據(jù)流通過程中,存在一個票據(jù)變造前和變造后權利該如何確認的問題。
對此趙新華教授指出,簽名的變造即屬于偽造。變造屬于記載問題,簽章屬于偽造問題。票據(jù)變造的舉證責任在票據(jù)法上非常重要。根據(jù)《票據(jù)法》第14條第3款的規(guī)定,不能辨認簽章人是在票據(jù)變造前還是變造后簽章的,視同在變造之前簽章。鄭孟狀教授認為,這樣的結果不利于持票人權利的保護,反而有利于變造人。例如,A簽發(fā)一張500元本票交付給B,B將票據(jù)金額500元變造為5000元轉(zhuǎn)讓給C。出票人A認為自己簽發(fā)是500元,而C目前所持票據(jù)為5000元,在雙方各自舉證而無法辨認的情況下,A按照第14條第3款的規(guī)定,對變造前的500元負責。而B將票據(jù)轉(zhuǎn)讓給C的時候從C處獲得了5000元的對價,其結果不利于持票人利益保護反而有利于變造人。所以建議將第3款修改為:不能辨認簽章人是在票據(jù)變造前還是變造后簽章的,視同在變造之后簽章。這樣的調(diào)整,可以保護持票人的權利。
對于這一問題,我國臺灣地區(qū)施文森大法官指出:“由于中國文字的原因,把四千五百元變造為十千五百元是很容易的。臺灣就出現(xiàn)過這樣的人,把四千的千字改為十,百改為萬字,做得天衣無縫,銀行在審查的時候沒有發(fā)現(xiàn)破綻,結果支付了十千五百元。銀行只要證明自己付款的手續(xù)中沒有重大過失就行。圍繞大陸票據(jù)法的規(guī)定,在前述的事例中,A是出票人,B在拿到票據(jù)以后,已經(jīng)把500元改為5000元。現(xiàn)在C的問題是,拿到的票據(jù)是先變造后簽名的還是簽名后變造的。臺灣判例的做法是要分清簽名在變造前作出的還是變造后作出的。票據(jù)到C手中時500元已經(jīng)變成5000元了。這多付的4500元損失一般可由支付代理人銀行承擔。因為銀行一般都會加人保險,減損的方法就是將損失轉(zhuǎn)嫁給保險公司。不管是從國際商事慣例還是從銀行慣例來講,銀行承擔這個責任都是明確的。可是內(nèi)地的做法有些問題,銀行往往在支付票據(jù)金額以后辯稱自己沒有重大過失而免責。雖然銀行的責任減少了,但是這樣的做法是很荒唐的。”